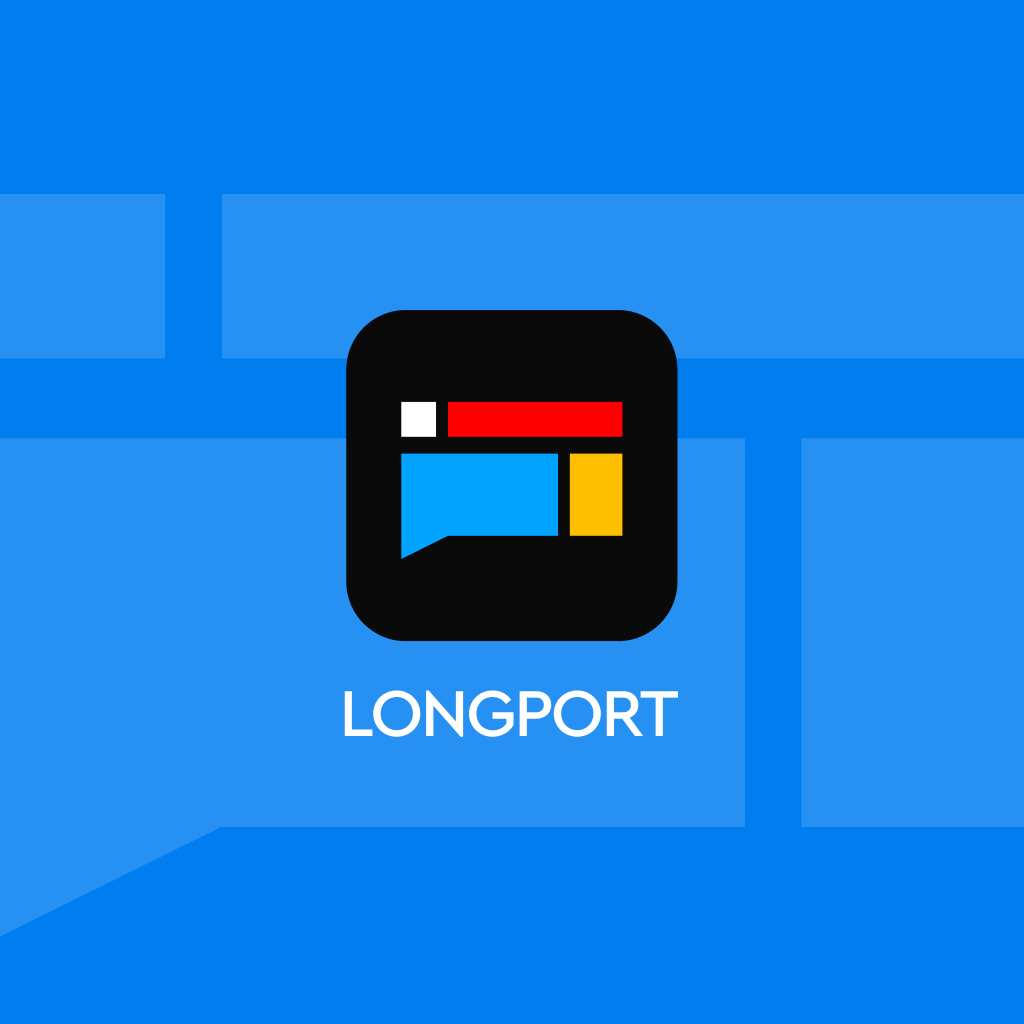
中国人在新加坡:富豪 party 夜,创业梦醒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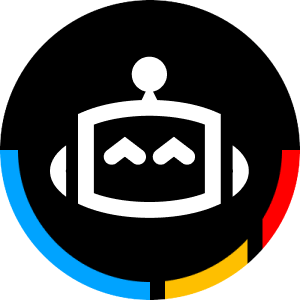
在 2022 年的新加坡,用中文聊 web3.0,喝黄釉瓶茅台,以及读一本名为《大衰退》书,都是正经事。
本文来源:36 氪,作者:袁斯来
要在新加坡寻找中国创投圈大佬,最好从餐桌开始。
即便坐在乌节路餐厅,中国人仍然固执地捍卫着自己的口味——比如对茅台的执念。
在每天不重复的酒局,通过酒的种类,大概能看出组局者的分野。新加坡当地人喝威士忌、红酒,中国创业小年轻喝啤酒,小有成就的新富豪饭桌上清一色茅台,有时白瓶中还夹杂更稀少的黄釉瓶茅台。参加的酒局够多后,有人已经能一口分出中国茅台和新加坡茅台的区别——“国内卖的酱香会更浓点。”
一位餐厅老板在朋友圈晒出卖茅台的汇款单:200 万人民币,还是预付款。他写下感激的话:“关键时刻大佬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 他停掉了清酒、大闸蟹业务,专心分销茅台。
一场酒局上,茅台成列。黄瓶茅台不是稀罕物。采访对象供图
除了喝酒,大佬们日常也有平淡些的小聚。有人就在街边大排档,看到字节跳动张楠和小米王川凑一起吃海鲜。如果喜欢踢足球,可以加入某个球局,前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最近几周都会出现。
一个国内亿级用户 APP 的老板在工作间隙,会在家里组局吃榴莲。七八个人光脚围坐,客厅里弥漫开甜腻的水果香气。其中有个人总是出现在同一个富豪身后,一问,不是家里人,卖保险的。
这是新加坡华人圈的另一种生态:不少富豪身边都会跟个保险经纪人。各种组局上,经纪人必须善于活跃气氛,比如德扑打到兴起,大家要玩真心话大冒险,保险经纪人会毫不犹豫跳上牌桌,跳一段性感的 table dance。
一些新来者很走运,仍能远程操纵国内业务。而一些前辈企业家们,已经开始习惯遗忘往日的荣光。几个前些年退休的大佬有个微信群,叫做 “二把手俱乐部”。其中一个曾经将公司做到行业前二后卖掉。退隐新加坡多年,他似乎很无聊,因为除了在家做饭、带孩子,时常能在各种饭局看到他。另一个人是上市公司前高管,据说喜欢和 web3.0 圈子打德扑,还 “玩儿得很大”。
有些更有名的人物过于难以接近,只出现在闲谈碎语中。比如雇佣私人飞机跨洲接送自己的张一鸣,据说在新加坡调养。有人听说 Top 大厂的创始人在新加坡避了一段时间风头。在 AI 圈子里则疯传,行业头部公司的高管们组团待在新加坡。
“新加坡就像在开大展会。类似于国内一个酒店扩大无数倍,里面全是大佬”,一个老创业者对 36 氪总结。
在这场 “大展会” 里,人来人往,整个城市沉浸于金钱的潮汐之中。
但对想尽快做点成绩的人,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空洞,到最后甚至让人厌倦。
一个来到新加坡的创业者说,原以为新加坡创业氛围很浓郁,呆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怎么天天都是大佬游艇 party,酒局,大家喝酒、抽雪茄,在甲板上友好地聊完一圈,然后呢?“啥都没有,ROI(投资回报率)太低”。
游艇 party 常见项目:海上看落日。采访对象供图
呆了几年的过来人,早就对这种落差习以为常。他们多少会带点看戏的心态。一个 FA 告诉我:“你最好明年 1 月再来看看,说不定很多人就回去了。”
高档中餐厅和豪宅外,隐秘的不安在一场场聚会和一杯杯咖啡之中蔓延。水滴筹 CEO 沈鹏在一场线下分享中说,自己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发现人人都在读辜朝明的那本《大衰退》。
但无论如何,2022 年,源源不断的新人持续涌入新加坡。他们的兴奋撑起了新加坡的喧哗和骚动。
一切到 9 月迎来高潮。
1、新加坡,“看上去” 很美
新加坡绝对不缺钱。但想从富豪手里拿到钱,绝不比在中国更容易。
最开始,说起去新加坡,投资人 John 有些不情愿。
一旦确诊,可能会困在国外一个月,这还不算回国隔离的时间。
但没有哪一个中国投资人会对 9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 Super Return 熟视无睹。
疫情开始的三年来,这是第一个全球知名 LP(出资方)会同时出现在线下的大会。9 月那一周,新加坡可能是整个亚洲财富最集中的城市。500 多个衣饰得体的欧洲、亚洲人穿梭在金沙湾会展中心,他们背后是手握重金的资方——南洋理工大学、阿布达比主权基金、大保险公司或者面目不详的高净值个人。
今年 John 所在的基金还没到募资期。大会开始前一周,John 的老板还在犹豫要不要到跑这一趟。但翻看同行的朋友圈和各自的聊天记录,老板无法再保持淡定:新加坡无处不在。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落后)的情绪终究还是占了上风。在 Super Return 开始前一周的例会上,老板终于拍板,“咱们还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可他自己是不愿意冒风险的,结果是 John 这个新合伙人辛苦一次。
三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同行之间聊天,压力大是逃不掉的话题。连 top20 基金创始人都会感叹:“今年压力大,主要在搞钱。” 即便还没有到募资期,John 必须出现在老出资人们跟前。安抚之余,试探他们未来几年的投资意向。
他这一次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挖掘新的家办和中东 LP。“毕竟,现在宇宙的尽头是新加坡。“他有些嘲弄地告诉我。
John 落地已经是 Super Return 开始的第二天,比起那些一周前就出发的同行,他们基金可以说很不积极了。
从樟宜机场一路开向城市 CCR(Core Central Region),John 忽然进入了久违的汹涌人群。红色、金黄和蓝色霓虹灯闪耀在滨海湾的夜空,挂满彩灯的游船驶过漆黑的海面,泛起光斑。
等待他的是初秋气候已经温吞的新加坡,还有到处热气腾腾的流动盛宴。
从早上 9 点到深夜 12 点,乌节路辐射的,街角的咖啡厅、楼顶的餐吧,只要 John 愿意,他就能找到一场聚会。除了无处不在的 web3.0 创业者,又多出 2000 多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金融圈人。
Super Return 举办地在新加坡标志性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据说是全球造价最高的单体建筑。三栋塔楼与其说是酒店和购物中心的集合体,不如说是一座小型城市。整个酒店有 2561 个房间,45 个餐厅, 22 家酒吧,1 间博物馆,1 条运河,1 个四层赌场,170 个品牌的购物中心,其中包括 LV 在巴黎以外最大的旗舰店。
到 9 月中旬,金沙酒店房价已经炒到上万。John 只能到喜来登定了房间,普通大床房花了 5000 多元人民币。虽然也在市中区,但附近甚至找不到一家便利店。那几天,金沙酒店门口永远排着几十个人打车,他只能走回酒店。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挑高到 9 米的展厅,人的声音也变得稀疏。John 站在 4、5 米宽的走廊,眼前是平静的海面,新加坡海峡吹来的海风弥漫湿气,真正的现代气息、硬件簇新明亮。
新加坡金沙大酒店,空中花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开会第一天,John 在展厅来回走了不下 2 万步。
早在出发前,他就在大会 APP 上给各种类别 LP 发了几百条私信约见面。除了私聊,他想过在现场临时找出不认识的 LP。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同行寒暄后,他学会装作不经意地搜寻对面人的胸牌,找出 LP 名字下才有的小黑色五角星。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4 点,他见了二十多个 LP。
只是,中东大亨的钱没那么容易收入囊中。中东 LP 们的口味是过去中国美元基金陌生的。来自迪拜、阿联酋的大金主们对短期内十倍、二十倍的回报似乎没多大兴趣,他们会问 John 陌生的问题:你们如何帮我们提升社会发展水平?这让 John 惊讶之余,绞尽脑汁改变自己的惯常话术。
中东 LP 的钱可能只在此短暂停留,好在新加坡本土也并不缺钱。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新加坡会新增 500 多个中国富豪,他们将为这个国家带来至少 24 亿美元。
不止一个投资人都会提到同样的数据:今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从 2020 年的 400 个涨到 700 个,而 “家办” 最低的基金管理规模也提到了 5000 万新币。
实际上,“5000 万是不好意思开家办的。” John 告诉我。他这次见到了管理 3、4 亿美元的家办负责人,背后金主身家在 20-30 亿美元之间,也有国内前五互联网公司的 SVP(高级副总裁)。
他们同样不好捕获。很多家办刚落地新加坡,还有些摸不到门路,尽管他们的投资轨迹已经在世界地图上四处跳动。
“今天投个欧洲房地产项目,明天投个亚洲基金,后天投个北美互联网项目。” 连 John 都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投欧洲的房地产。” 对方回答:“因为老板和其他有钱人攒了个局,地产也是老板朋友的。”
在一个陌生的市场,如果家办管理人还没有完全获得老板们的信任,能做的是老板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就看什么项目。
以至于这些家办管理人自己都不敢保证对中国的美元基金多么了解,即便能叫出一个个基金的名字,却弄不清它们彼此间的区别。当 John 追问对方能投多少钱,他们只能含糊地说 “300-3000 万美元都是我们的范围。”至于能不能给钱,“回去得和老板商量,不确定老板喜不喜欢。”
新加坡看似遍地黄金,但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新加坡走马观花的半个月,真正调动起 John 情绪的事却和融资无关。
结束后,随之是 web3.0 圈里众人皆知的大会——Token 2049。这场大会真正点燃了新加坡。
那几天,在新加坡的投资人,很多朋友圈都被 Token 2049 刷屏,夸张点的分享和圈里名人的合照,普通的分享则是人满为患的咖啡厅,反正都是些搞大事的画面。
有些活动直接办在夜店,台上兼职当 DJ 的 web3.0 创业者打碟,鲜艳的灯光闪烁不停。在各种 web3.0 群里,他们晒陈柏霖、林俊杰、伊能静的照片。
场面实在太过盛大,以至于有个提前离开的投资人很快开始后悔:开始以为 Token 2049 只是个规格比较高的会,有些活动而已,没想到是个 “大 party”。
“你在国内真体会不到这种氛围,还是很酷的,千禧一代以后的感觉。” 这个投资人告诉 36 氪。
John 原本只是带着些看热闹的心态加入,但到那一周结束时,他已经参加了 40 多场活动。如果和活动上的 web3.0 创业者聊得对味,他可以在凌晨 2 点约海底捞,一直吃到天色将明。“web3.0 没有夜晚,” 他说。
Token 2049 活动现场。图片来自官网
前一周在金沙会展中心,John 擦身而过的很多白发苍苍的投资人,被中老年人包围太久了后,John 怀疑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放眼 token 2049,几乎都是年轻鲜嫩的脸孔。“这对比真的是太强烈了。”
在 Token 2049 间隙,John 去了次创投圈聚会。聚会在当地算得上高档的中餐厅举办,或许是为了凸显中国元素,进包间就能听到传统民乐,铜锣唢呐一派喜庆,还以为春节提前了几个月。
包间里近百号人,基本都是互联网投资人或者新加坡银行、政府的官员。最近很活跃的金沙江合伙人朱啸虎,自然没有缺席,还能看到软银、淡马锡和中东基金的人。
或许是为了照顾本地人,桌上没有茅台,只有红酒。大家有礼貌地聊天、敬酒。要有人问起 “你最近关注什么?” 通常只会收到平淡的回答:“没什么投的,也没什么关注的。” John 受不了沉闷的氛围,呆了一个小时就退席,跑去参加 web3.0 活动直到半夜。
但狂热的 party 之后,John 无法忽视矛盾之处。就算手里没有数据支持,他也凭直觉知道,眼下的新加坡,投资人比靠谱的 web3.0 项目多。“这场会,对我这种不太了解的黑子是破圈的机会,但好的项目比例很小。”
这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普遍感受。2022 年新加坡创投圈,最多的是投资人,但钱和好项目却都难找。看上去满地机会,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为 “梦想” 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买单。
2 浮华背后
一个创业者奔赴新加坡时,如果想重新看到中国 2015 年时 “万众创业” 期的盛况,必然会失望。全球经济衰退时,新加坡只不过比亚洲邻居表现好一点,并不会幸免。
新加坡的水温已经开始下降。Token 2049 人潮涌动,新加坡互联网圈子聊的却是大裁员。
当 John 到达新加坡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创业者 Paul,已经决定关掉公司。
如果看履历,Paul 算是在东南亚有经验的中国创业者。他在本土头部公司当过中层,说很流利的泰语、英语、印尼语。自己做的电商项目,之前还拿了点知名机构的融资。
8 月末的早上,Paul 刚醒来,发现平静很久的虾皮离职员工群,忽然 “噼里啪啦” 进来一连串刚被裁掉的人,群里一片喧闹。那些人告诉他,有十多年历史的实验产品孵化部门没了,一个人不剩。
Paul 当时正为自己项目找下一轮融资,找到头发花白。看到消息时,他知道大势已去。连头部公司都降低预期不再投入新项目时,自己没有必要继续挣扎。
Paul 有很多找钱的渠道。他交游很广,认识很多有钱人,也和本土基金关系不错。
老板们很乐于在宴会上看到他。新加坡呆了很多年的老江湖曾带他去私人会所。Paul 曾听说美团的前几号人物和朋友来过这里聚会。会所落在别墅和私人公寓林立的丘陵地带,门外看不到任何招牌,也不会对外营业。
刚一进门,他就看到的是横七竖八停放的豪车,最显眼的是辆黑色劳斯莱斯,方形车头上的欢乐女神像银光闪耀。车辆停放随意,见缝插针塞满并不宽敞的院落,“看着像香港电影里黑帮的聚会。”
忙的时候,Paul 一个月在家吃饭的次数五个指头数得过来。但和他忙于奔命不同,大佬们似乎不太着急于追逐事业第二春。他听到营收千亿的上市公司前总裁在私人聚会上表示,我们在欧洲投了一个亿,东南亚也该布局了,现在也有牌照,就是不知道做啥,“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也来看看。”
“看看” 是很多富豪的心态。“我不投钱我也不做什么,就在那里花曾经赚的钱。” Paul 这样总结。
毕竟新加坡至少在眼下能给大佬们足够舒适和安全的生活。
新加坡圣淘沙海港,游艇拥挤。采访对象供图
Paul 有时会被朋友邀请,去中国互联网圈子老板们很热衷的住宅区参加聚会。几个相近的小区中,户主包括曾经某行业排名前三公司的创始人、头部基金合伙人。最近,户主还多了个社交独角兽公司创始人,她刚到新加坡不久。
小区门外就是繁华的 CBD。房子大多只有十多层高,大楼配色和外观看似简单,但正好完美搭配院落里的棕榈树。院中 50 米长、8 条水道的泳池永远蔚蓝,池边蓝色遮阳伞下,黑色躺椅空无一人。
看惯一线城市高层住宅的人,都知道如此疏落的布局,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是一种真正的奢侈。
新加坡四处飘散着这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为草芥的金钱气息。但它们解不了 Paul 的困局。比起给创业公司投钱,老板们宁可去投资些本土房产金融产品。投资人总是礼貌地说:“你去找领投吧,有领投,我们也跟一些。” 有投资人更直接:“你项目就算不错,也很难撑过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真正的好时候已经过去。即便在亚洲此刻最热门的城市新加坡,景气度也已经不复从前。
在中国投资人们蜂拥而至前,以美国放水为节点,软银、Tiger global、DST 就在新加坡大肆扫项目。一个当地投资人总结:“之前他们都没什么存在感,这两年出手大,出手快。”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被投资人们戏称为 “接盘侠” 的国际大基金,在 2021 年经历被投公司 IPO 血亏后,开始 “躺平” 了。
这样一来,似乎突然之间,在新加坡做到 B 轮 C 轮的创业者,发现自己找不到钱了。
一个已经盈利的 AI 公司,做了七八年,到今年,愿意再投下一轮的投资人消失了。创始人找到一家基金的老大,对方甚至不愿意开个价格,“开不了”。
基金们看项目时热情有多高涨,转瞬之间掏钱时就有多谨慎。
John 就在新加坡拒掉了一个中国高管的创业项目,他认为市场太小,对方要价又太高。而此人在圈子里还有些名气,曾经在国内经手过类似的生鲜头部项目,一路做到了高管。当他为融资四处奔走时,圈子里传开五味杂陈的流言:“你看,连他都找不到钱。”
新加坡 marina 海湾和商业中心的清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似乎只有 web3.0 圈子的热情从未消退。
在市区,甚至当地房地产商也搞起 “元宇宙 +web3.0” 活动。售楼处的沙盘描摹出价格 3000 多万人民币高端公寓的样子,LED 屏幕打出 web 3.0 的活动海报,沙盘旁摆放百来把座椅。场地有些简陋,但挤满了人。
如果到新加坡麦里芝水库附近的绿道,最常见的是 web3.0 圈子的徒步。夸张的徒步活动,可达浩浩荡荡一百多人。他们会冒雨在步道走几个小时。三五个人一排,队伍黑压压一片,整齐出发后如同行军,彼此还要提防雨伞的碰撞。
有些活动则走华丽路线。赛马场普通看台旁,穿拖鞋短裤的中年男人攥着马票,睁大眼睛拼命想看清远处屏幕上的小字。但在 vip 包厢的 web3.0 聚会,头顶屏幕就滚动着实况字幕和直播画面,落地窗外可以清晰看到终点线。房间内红色地毯柔软厚重,沙发是丝绒套。女人们妆容细致,短裙配高跟鞋,男人们则西装革履。安静的房间上空,币圈黑话飘来飘去。
但这场浮夸背后,注入太多水分。
或许是出于同行相轻,美国 web3.0 圈会嘲笑新加坡的圈子:“新加坡十个项目九个骗,还有一个在路上。”
那些拿了融资的公司,往往有着神秘的面孔。一个 web3.0 创业者告诉我,他们前后融了 1000 万美元,但前两轮都是代币。具体架构如何,他 “不方便透露”。
同样神秘的,还有这群创业者的生活。他们会告诉我,自己生活很简单,不爱到处聚会,生活很健康,最多就是去徒步、打网球。但其实饭桌酒局间,少不了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抛开这些真假掺半的谈话,如果只讨论业界话题,一切都让人兴奋。饭局上,大家聊起谁又成了独角兽,谁又募了 100 亿 (token),“真是独角兽都不够用了。” 一个在新加坡看 web3.0 项目的投资人调侃道。
可圈中一些行为让他很不喜欢。做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乍富的联合创始人,新买了辆劳斯莱斯,在新加坡街头无比抢眼,而且他的豪车不止一辆。这样以豪宅、游艇为标配的造富速度差不多要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
他算是个老投资人,这种场景和对话似曾相识。“怎么和当年 P2P 骗局的时候一样?还没成功就开始高消费了?” 至于交易所,他断言:大部分 “就是赌场”。
找到稍微靠谱的项目真如同大海捞针。好不容易聊到下一步,没想到项目方很快又开始发币、ICO。“太容易割韭菜,A 轮就发币,上市,套现,然后买个豪车就玩吧,诱惑实在太多了。” 他告诉我。
6 月中旬,加密货币贷款公司贝宝告诉合作伙伴 “我们已经资不抵债”。接下来,不少豪车从新加坡街道消失。
创始人亡命天涯的故事也开始流传。饭局上,朋友有些遗憾地宣布:“本来今天要介绍某人给你认识,但昨天他出事儿,来不了了。”
这个投资人一直没能见上那些年轻高调的 web3.0 传奇人物,说实话他也没兴趣再见。他看起了传统的互联网项目,再提起 web3.0,他会摇摇头:“太早了,市场太小了。”
3 败兴而归
度过了几个不眠夜后,John 已经考虑离开新加坡,尽管他在市中心的咖啡厅,还时常碰到熟面孔,都是些中国的美元基金投资人。
金沙江的朱啸虎有时还出现在 web3.0 大合照里,有时被人看到在机场等待。Paul 戏称:你在新加坡飞中国的飞机上问一嗓子有没有投资人,一定会有人搭腔。他座位背后,就坐了个头部基金投资人,两个人后来的话题之一就是比惨。
美元基金们纷纷张罗着开设新加坡办公室,哪怕现在根本招不到当地负责人。因为当地的管理人才 “都在本土和国际大基金”。
中国投资人们偶尔的大动作,会让其他投资人感到匪夷所思。有个投资人看到中国同行投了某大佬的创业项目,给了上千万美元天使轮,而他们看过的类似项目,估值更加便宜。这样一来,对方出手的逻辑就显得奇怪了,“就觉得挺离谱,投资不能只看报表。”
如果穿透过这场盛会的外壳,会发现那些为利忙碌的熙熙攘攘,实际上很少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更多人似乎是被环境 “逼” 到新加坡。
“新去的(投资人)都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这个公司看到那个公司,所有的地方如数家珍,谁都认识,谁都知道,工作就完成了,报告也能写了。” Paul 说。
没人知道新加坡的喧闹能持续多长时间。一个 FA 就告诫自己的朋友:“你过来看可以,但是国内的业务不能丢,不然你在东南亚投不出项目,回去团队就没有你位置了。”
这位 FA 告诉我,他接触过一个基金高层,开会时高层直接扔来两个问题:“你说下东南亚哪些投资人比较活跃?每年案子有多少个?” FA 觉得奇怪:“你怎么不查查报告?都是公开的数据,怎么问我这个问题?” 对方很不客气地回答:“我都知道了还来问你干嘛。”
最近流入新加坡的钱还是太年轻。说到底,新加坡进到金融中心前三也就是今年刚发生的事。
新加坡最高建筑 Gucco 大厦三层顶层公寓由华人廖凯原买下,他也是特斯拉最大个人股东之一。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9 年,John 在香港跟着老板募资时,新加坡在资本圈还是个不入流的城市,资本流动性差、没什么创业生态,谁要说起去新加坡上市,圈里人第一反应是 “为啥去新加坡?能有什么好处?” 一位投资人 2018 年跳槽到新加坡基金,他记得中国来的 VC“五根指头数得过来”,投一个东南亚本土项目,他们可能是唯一一家有中国背景的资方。
事实上,当时除了腾讯、字节的战投部,很少有机构看得上东南亚。
相比之下,合伙人们在香港会停留更长时间,机构可能只派个 associate(助理)级别的中层在东南亚粗略扫一圈,回国在会上推荐一下,整件事通常以 “推不动” 告终。如果有份东南亚的创业项目书到了投资人面前,投资人会一脸质疑:你真的熟悉这个市场吗?潜台词是:“我觉得不靠谱”。
蜂拥入新加坡的很多人更多是追逐热点和宽松政策而来,比如 web3.0。但到底怎么在这里做生意?大家没有答案,没有底气,也没有定力。
未来该往何处去?暂时也无清晰答案。John 和同行一样,没人会把那本《大衰退》摆在桌上,但他欺骗不了自己:“有些行业就是到了末路,比如中国在线教育,比如欧洲的房地产。”
9 月末,John 的新加坡之行已经兴味阑珊。他离开新加坡回国,坐在隔离酒店,显得更加冷静:“目前的挫折是阶段性的。香港很快就能恢复,它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很重要。新加坡毕竟体量太小,那里不是我的重点。”
他还记得 2019 年参加香港万豪酒店的 Super Return。走廊灯光昏黄陈旧,三十年历史的欧式雕花扶手、色泽浓郁的地毯,又增加了沉重感。人群挤在狭窄大厅,蒸发出的汗气让空气濒于凝滞。这和新加坡金沙酒店的宽阔簇新全然不同。可 John 还是怀念香港,起码在那个老牌金融中心,“你想象不出来,只是多了几千个人,酒店价格就崩溃了。”
(根据采访对象要求,Paul、John 为化名。感谢 36 氪作者刘旌、任倩、于丽丽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