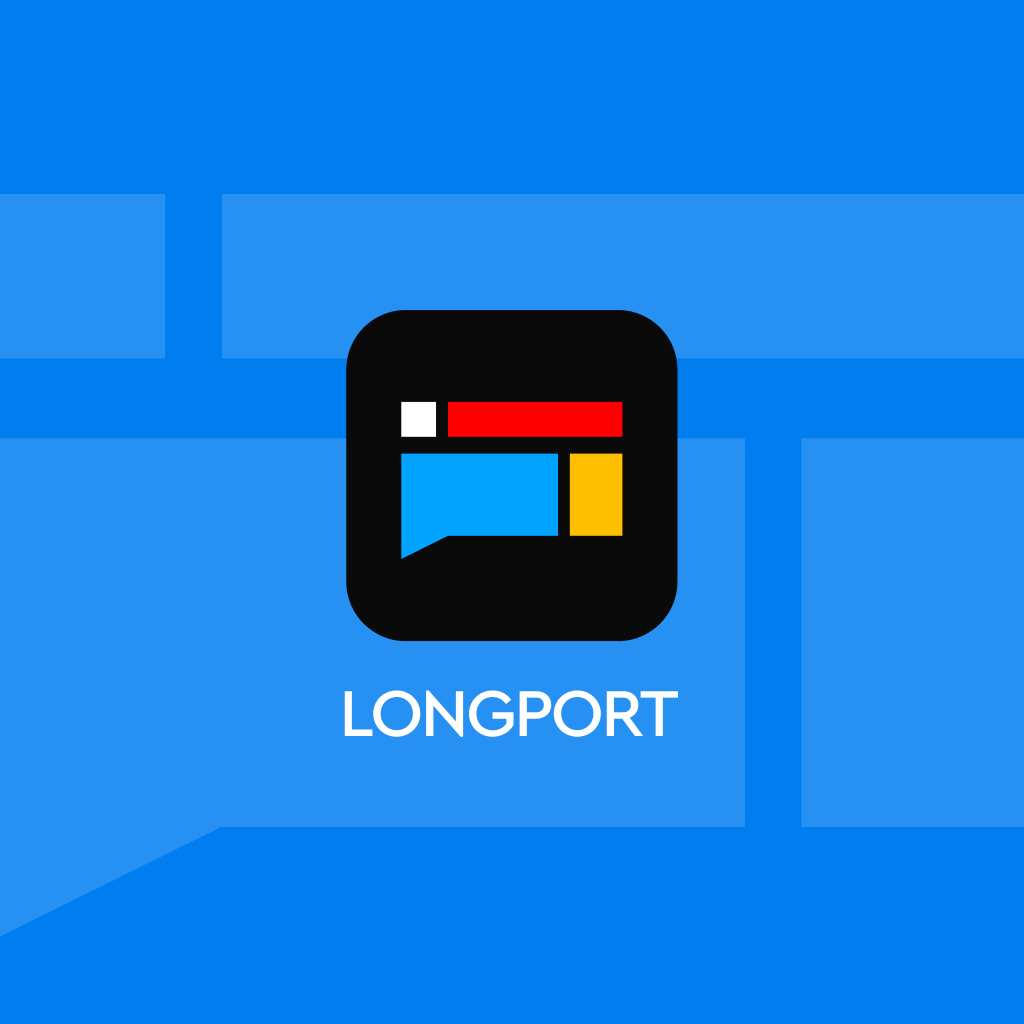
As "AI programm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easier, a new wave is emerging: "micro-applications" that anyone can create and "super programmers" who can replace entire teams

對於大眾,軟件開發權正在下放,編程變得像發微信一樣簡單;對於從業者,平庸的中間層正在消失,唯有那些能駕馭 AI、一人抵一軍的 “超級個體”,才能立於潮頭。
硅谷正在瘋搶一種被稱為 “Cracked Engineers” 的新物種。
在 AI 淘金熱籠罩下的灣區,傳統的招聘邏輯正在失效。機器人初創公司 Gradient 的聯合創始人 J.X. Mo 直接取消了公司的實習生招聘計劃。理由簡單而殘酷——沒人足夠 “Cracked”。
在他看來,在 AI 輔助編程的時代,如果一個新人不夠 “Cracked”,不能如遊戲高手般狀態炸裂、技術精湛且不知疲倦,就不配擁有一張工牌。
在 AI 把編程的門檻無限拉低的今天,全球軟件行業正在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兩極分化。
一方面,編程的門檻正在無限降低。得益於 Claude、ChatGPT 等工具,不懂代碼的普通人開始通過自然語言構建極度個性化的 “微應用”(Micro Apps),軟件正在從一種需要購買的 “商品” 變成一種可以自制的 “工具”。
另一方面,專業工程師的競爭也愈發激烈。在硅谷,初創公司正在瘋搶前文提到的 “Cracked Engineers”(硬核工程師)。這羣年輕人利用 AI 將個人產出放大至極限,試圖以一人之力替代整個傳統開發團隊。
人人可做的 “微應用”:從 “訂閲 SaaS” 到 “自制工具”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如果你需要一個軟件來解決特定問題,通常你會選擇是去 App Store 下載或購買 SaaS 服務。但現在,一種新的消費習慣正在形成:自己造一個,用完即走。
這種由非專業開發者構建的軟件被稱為 “微應用”(Micro apps)或 “一次性應用”(Fleeting apps)。它們的特點極其鮮明:場景極度垂直、解決即時痛點,且往往不具備商業推廣意圖。
霍華德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 Legand L. Burge III 將其比作社交媒體上的快閃趨勢,只不過這次的主角是軟件本身——“當需求消失時,軟件也隨之消失。”
Rebecca Yu 的故事極具代表性。
為了解決朋友聚餐時的 “選擇困難症”,她在沒有任何技術背景的情況下,利用 Claude 和 ChatGPT,僅用七天時間,她就 “搓” 出了一個名為 Where2Eat 的 Web 應用,這個應用能根據她和朋友們的共同興趣推薦餐廳。
在過去,這往往需要僱傭專業的全棧工程師,或使用複雜的低代碼平台才能完成。
Rebecca Yu 説:
“一旦我學會了如何高效地向 AI 提問(Prompt)並解決問題,構建過程就變得容易多了。”
(1)填補 Excel 與 SaaS 之間的真空
貝恩資本風投(Bain Capital Ventures)合夥人 Christina Melas-Kyriazi 敏鋭地指出,微應用正在填補 “Excel 表格” 與 “全功能 SaaS 產品” 之間的巨大市場真空。就像當年 Shopify 讓開店變得簡單一樣,AI 正在讓軟件開發變得像做表格一樣隨意。
人們開始為極其垂直、甚至可以説 “瑣碎” 的需求定製軟件,類似的案例正在硅谷爆發式增長:
- 醫療記錄: 軟件工程師 James Waugh 為患有心悸的朋友開發了一個簡單的日誌記錄器,專門用於向醫生展示心臟數據。
- 生活瑣事: 媒體策略師 Hollie Krause 因為不喜歡醫生推薦的 App,自己動手寫了一個過敏症追蹤應用。她形容其開發速度之快:“我丈夫出門買個晚飯回來的功夫,我就寫完了。”
- 一次性娛樂: 創始人 Jordi Amat 為家庭假期聚會開發了一款網頁遊戲,假期一結束,這個 App 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被直接關閉。
- 惡習追蹤: 一位藝術家甚至開發了一個 “惡習追蹤器”,專門記錄自己週末抽了多少水煙、喝了多少酒。
(2)“用完即走” 的商業悖論
SBS Comms 副總裁 Darrell Etherington 預言,未來人們將停止訂閲那些按月收費的工具應用,轉而根據具體需求,利用 Claude Code、Replit 或 Bolt 等工具 “自給自足”。
然而,這股浪潮並非沒有阻力。雖然 Web 應用的開發門檻已降至零,但移動端 App 仍面臨 “蘋果税” 的阻礙——每年 99 美元的開發者賬號費用對於一個 “一次性應用” 來説過於昂貴。
不過,資本市場已經嗅到了機會,像 Anything(獲 1100 萬美元融資)和 VibeCode(獲 940 萬美元種子輪融資)這樣的初創公司,正致力於解決移動端 “Vibe Coding” 的最後一公里問題。
當然,這些個人開發的軟件在質量、安全性和維護上存在天然缺陷,它們註定無法規模化銷售。但對於創造者而言,它們不需要服務大眾,只需要服務自己——這本身就是對軟件產業原有供需關係的顛覆。
一人頂團隊的 “超級程序員”:AI 時代的 “Cracked Engineers”
如果説微應用是編程門檻降低的產物,那麼 “Cracked Engineers” 就是專業從業者激烈競爭的縮影。
“Cracked” 一詞源自遊戲圈黑話,形容那些操作神乎其技、狀態 “炸裂” 的高手。
在如今的硅谷,它被用來定義 AI 時代最理想的軟件工程師形象:年輕(通常 20 多歲)、極度渴望成功、技術嗅覺敏鋭,且能利用 AI 工具實現驚人的產出。
機器人初創公司 Gradient 的聯合創始人 J.X. Mo 最近做了一個殘酷的決定:取消實習生招聘。在面試完申請者後,他發現 “不值得浪費時間”——因為沒人足夠 “Cracked”。
在 AI 淘金熱的背景下,初創公司追求極致的人效。Turing 公司 CEO Jonathan Siddharth 認為,藉助 AI,一個小而精的團隊完全有可能在一年內將營收做到 1 億美元。創始人不再需要按部就班的平庸代碼工人,他們需要的是特種部隊。
這裏的 “Cracked Engineers” 與我們熟知的兩類人有着本質區別:
- 他們不是 “Vibe Coders”:Vibe Coders 往往缺乏底層技術根基,只是 AI 的 “提示詞操作員”(Cursor Jockeys)。而 Cracked Engineers 擁有深厚的技術造詣,他們利用 AI 大幅提升效率,但同時具備審查和修正 AI 錯誤代碼的能力。他們是駕馭 AI 的騎手,而非乘客。
- 他們不是傳統的 “10x Engineers”:上一代科技圈推崇的 “10 倍工程師” 通常在 30 歲以上,就職於 Google 等大廠,遵循流程,甚至對 AI 編程工具持保留態度。而 Cracked Engineers 更年輕、更具反叛精神,他們對大廠的政治鬥爭不感興趣,信奉 “工作即一切”。
“一人頂一隊” 正在成為現實。
Intology 的 CEO Ron Arel 指出,幾個極度專注並善用 Claude Code 的人,現在的產出能超過以前沒有 AI 輔助的 15 人團隊。
Far.AI 的聯合創始人 Adam Gleave 透露,他的一名員工在 AI 輔助下,僅用幾周時間就完成了原本需要開源社區耗時一年才能完成的大模型微調軟件原型。
這種高產出往往伴隨着極致的工作強度。這些工程師普遍接受甚至推崇 “9-9-6” 的工作模式(早 9 晚 9,一週 6 天),因為他們深知在 AI 競賽中,慢一步就是淘汰。
PostHog 的聯合創始人 James Hawkins 這樣描述他們:
“他們不在乎辦公室政治,不在乎穿衣打扮,甚至不修邊幅。工作成果説明了一切。”
然而,這種對 “超級程序員” 的狂熱追逐也暗藏隱憂。
孟羅風投(Menlo Ventures)的合夥人 Deedy Das 觀察到,一些年輕工程師為了顯得 “Cracked”,開始刻意表現出反社交傾向,使用晦澀的語言,或者為了工作放棄所有愛好。他提醒道:
“最有效的技術領袖往往是善於溝通的,這不是一個單人遊戲。”
招聘專家 Kelsey Bishop 更是直言不諱:許多創始人試圖用招聘一個 “Cracked Engineer” 來掩蓋商業模式的缺陷,“他們把這當成一種創可貼,但這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結語
當 AI 編程變得越來越容易,中間地帶正在消失。
對於普通用户,軟件開發權正在下放,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的 “產品經理”;對於專業領域,門檻正在被無限拔高,唯有那些能駕馭 AI、將肉體與算法結合的 “超級個體”,才能在激烈的淘金潮中生存。
這是黃金的時代,也是殘酷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