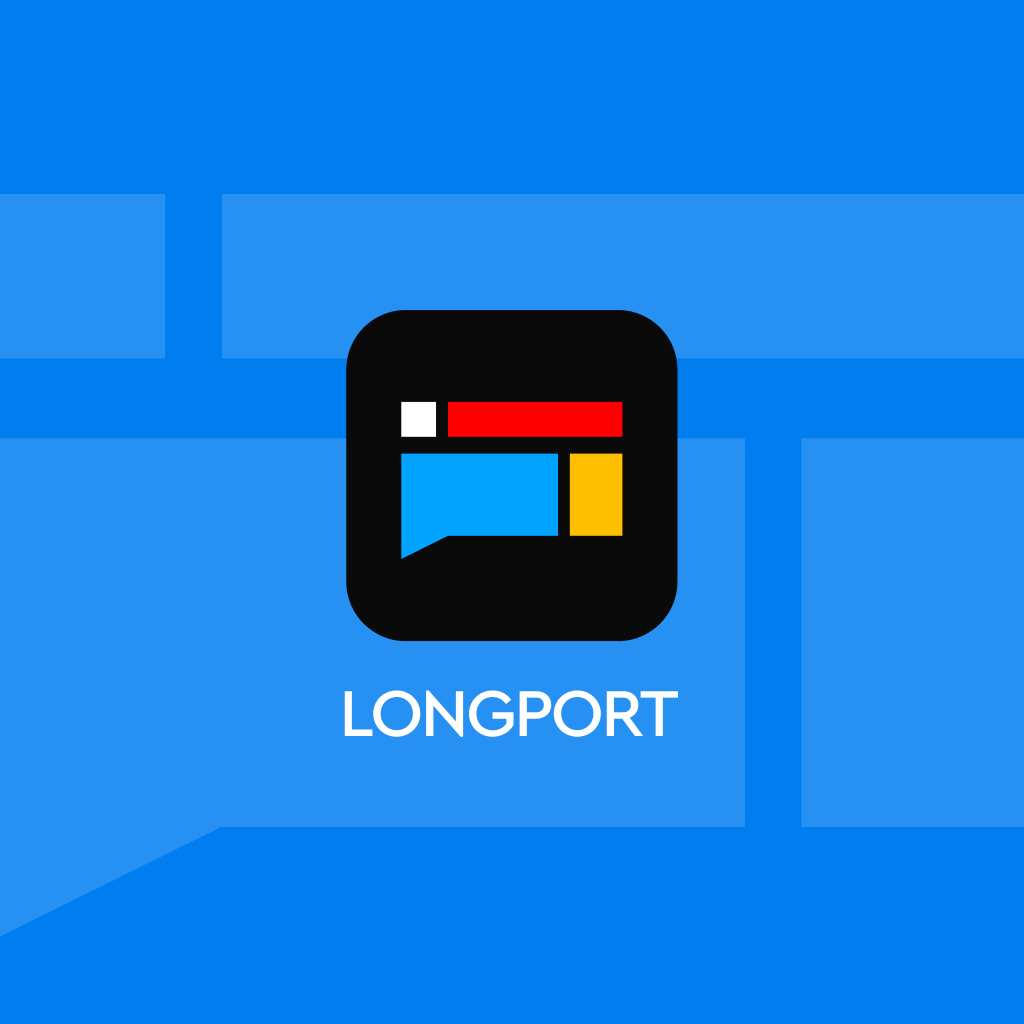
聲音的戰爭

海外音頻社交軟件 Clubhouse,因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的使用,註冊用户從 1 月下旬的 200 萬以裂變方式持續飆升,迅速成為互聯網社交領域的新寵。
來源:奇偶派
作者|田歡子
編輯|王十
海外音頻社交軟件 Clubhouse,因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的使用,註冊用户從 1 月下旬的 200 萬以裂變方式持續飆升,迅速成為互聯網社交領域的新寵。
近日,華爾街著名空頭機構香櫞連發兩則推特,唱多去年初美股上市的 “音頻第一股” 荔枝,一時間,沉寂已久的荔枝股價暴漲 350%。荔枝旗下音頻社交軟件 Tiya 和 Clubhouse 有異曲同工之妙,香櫞唱多荔枝的原因正在於此。
國內音頻行業十年漫漫,一直承受着不少質疑,諸如,商業模式變現力弱、內容生態是否具備護城河、資本對耳朵經濟的低感知,這些也都是行業內幾家頭部公司的隱痛。
但近年來,在線音頻行業的整體價值是向上的。據安信證券研究中心最新報告顯示,2023 年全球在線音頻市場規模將從 2018 年的 105 億元增長至 307 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為 23.8%。此外,中國作為全球擁有最多在線音頻用户的國家,2023 年我國音頻用户將從 2018 的 3.77 億上升至 9.02 億,複合年均增長率為 15.7%。
行業的整體用户的基本面在變大,但數據顯示,整個長音頻的行業滲透率始終就是 8 個點左右。互聯網發展過於迅猛,時間殺手短視頻平台快抖拔地而起,音樂巨頭 TME(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看中了音頻喜人的時長,認定互聯網最終是一個時長的爭奪戰,於是帶着希望音頻破圈、提高行業滲透率、完善業態鏈的態度,強勢入局音頻行業。
不久前,音頻行業老廠牌蜻蜓 FM,在戰略會上總結音頻行業的上一個十年,在內容供給裏,很明顯的一個瓶頸或者固有慣性是,大部分音頻內容的紅利和內容不是來自於音頻原創,而是對已有成熟的其他內容媒體類型的遷移。
顯然,音頻行業的頭部平台們意識到,自己正在淪為聲音內容的搬運工,而聲音的內生價值,到底又在哪裏?
01
聲音的春天真來了?
Clubhouse 火爆全球,熱鬧之下,沉寂已久的音頻行業真的要迎來春天了嗎?
此前,華爾街著名空頭機構香櫞連發兩則推特唱多荔枝。香櫞對荔枝旗下的應用程序 Tiya 表示出濃厚的興趣,Tiya 是荔枝於 2019 年孵化的一款主攻歐美市場的音頻社交軟件。香櫞推文的視頻資料顯示:“Tiya 在全球 70 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交 APP 中排名前 10 位,之前專注於遊戲,目前已經擴展到約會社交領域。”
荔枝有機會從中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趨勢中受益,所以給出荔枝的目標價格應提升至 30 美元。

唱多的推文發佈後,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的荔枝股價短線拉昇,向上熔斷,當日收漲 29.5%,市值增至 6.31 億美元,換手率高達 137.35%。雅樂科技的股價當日也收漲 15.29%。
香櫞唱多荔枝,源於 Tiya 正處於當下備受關注的音頻社交賽道,Tiya 被視為中國版的 Clubhouse。年初,特斯拉 CEO 馬斯克在一款名叫 Clubhouse 的即時性音頻社交軟件上舉辦了一場語音直播,在直播的幾小時內,該軟件同時在線人數高達 5000 多人。
Clubhouse 一夜爆紅,直接帶動相關語音交友概念股股價直線飆升,受此影響,短短三個交易日,荔枝的股價暴漲 350%,但又迅速回調。
而據安信證券研究中心最新報告顯示,2023 年全球在線音頻市場規模將從 2018 年的 105 億元增長至 307 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為 23.8%。此外,中國作為全球擁有最多在線音頻用户的國家,2023 年我國音頻用户將從 2018 的 3.77 億上升至 9.02 億,複合年均增長率為 15.7%。
在線音頻行業在整體向上發展,荔枝借東風,進入大眾視野,但此前的荔枝,是受市場忽略的,去年一月,荔枝以 “音頻第一股” 的身份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上市,但上市即破發,從 11 美元一路跌至最低 1.9 美元。
從荔枝近年來的財報來看,這種低估並不是空穴來風。
財報顯示,荔枝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營業收入分別為 4.5 億元、8.0 億元、11.8 億元、15 億元,但增速在大幅下滑,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同比增速分別為 76%、48%、27%。
毛利潤方面,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毛利潤分別為 1.2 億元、2.3 億元、2.7 億元、3.7 億元,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年的同比增速分別為 90%、16%、36%。

增速放緩的營收增長,實有隱患。從 2017 年至今,荔枝還並未實現盈利,2017 年至 2020 年四年時間裏,荔枝的淨虧損分別為 1.5 億元、0.1 億元、1.3 億元、0.8 億元,四年累計虧損 3.8 億元。
虧損的背後,是荔枝一如既往的單一盈利模式和變現難題。
荔枝的運營模式區別於國內音頻行業主流模式的 PGC(專業機構產生內容),荔枝主打 UGC(用户產生內容) 模式,這兩者不同,PGC 產品由專業團隊製作,用户 “付費” 作為主要盈利模式,UGC 作品為網絡音頻直播,用户打賞讚助作為主要盈利。
招股書顯示,荔枝的營收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音頻娛樂收入,即向用户銷售與音頻娛樂有關的虛擬禮物;二是播客、廣告和其他方式。
在 2019 年、2020 年的財報中,荔枝的音頻娛樂收入佔比均高達 98%,2019 年、2020 年分別為 11.7 億元、14.81 億元,而播客、廣告和其他收入佔比均在 2% 以下,僅有 1266 萬元和 2180 萬元。業內人士表示,這也顯示出荔枝的收入渠道較為單一。
招股書中還提到,虛擬禮物的銷售主要受付費用户數量的驅動,在 2019 年財報中,荔枝的平均月度付費用户為 43.41 萬,同期的活躍會員數是 5190 萬,付費用户佔活躍用户的比例為 0.84%。2020 年,荔枝的月付費用户不增反降,為 42.24 萬,而會員數則增長到了 5840 萬,如此也拉低了付費用户佔比,這個數字為 0.72%。
用户付費率是評判在線音頻平台變現能力的一個核心指標,而荔枝的表現則顯得有點差強人意。但不管是 PGC 還是 UGC,數據顯示,未來三年,這兩者業務模式所帶來的 ARPPU(每付費用户平均收益)增長趨勢較慢。
根據安信證券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報告,2023 年我國音頻內容訂閲年度 ARPPU 將從 2018 年的 197.5 元上升至 279.5 元,複合年均增長率為 5.96%。反觀國內,2023 年,我國音頻直播年度 ARPPU 將從 2018 年的 422.1 元上升至 630.0 元,複合增長率為 6.90%。
相比之下,音頻直播 ARPPU 複合增長率略高於音頻內容訂閲,然而總體來看兩者複合增長率都偏低(低於 10%)。
單一的營收結構加上疲軟的付費用户數量增長,Clubhouse 的虛火很難燒熱荔枝這鍋水,荔枝,似乎並不能迎來那個想象中的明媚春天。
02
封閉無聲的賽場
荔枝受困於 UGC 模式帶來的單一營收結構和低緩的付費用户增速,那麼國內主流音頻平台的 PGC 模式會更好一些嗎?
早期,移動音頻業和大部分互聯網行業一樣,競爭焦點鎖定在內容和用户上,而彼時最底層的商業邏輯是一種簡單的 “場景更替”,將正在消失的電台媒介移植互聯網,這其中沒有顛覆性的肌理改造,可視為一種複製粘貼般的需求重塑,這也為此後長達 10 年的多舛命途埋下隱患。

簡單的搬運模式卓有成效,帶來內容和用户的增長肉眼可見,量大且速度快。很快,市場份額迅速在 2015 年底瓜分完畢,喜馬拉雅、蜻蜓 FM 和荔枝 FM 成為行業前三強。
在當時,音頻行業的格局模糊。喜馬拉雅最先摸清關鍵動作,接連發力版權內容、推出有聲讀物,很快在用户規模和行業佔有率上拔得頭籌,成為業內第一,同時也暗示着喜馬拉雅此後在行業內長期第一的位置。
分化出現在 2016 年左右。2016 年 5 月,以語音問答為主要形式的分答引爆了知識付費風潮。喜馬拉雅最先嗅到了風向的轉變,創始人餘建軍喊出 “音頻是知識的良導體” 的口號,帶領喜馬拉雅全面進入 PGC 模式下的知識付費。
這一年,喜馬拉雅開闢了付費專區,邀請了馬東、吳曉波等一眾 KOL 入駐,迎來了改變行業的爆款,上線了超過 200 個付費課程。年末,喜馬拉雅打造出首屆 “123 知識狂歡節”。其首日成交額達到 5088 萬,2016 全年喜馬拉雅的付費收入超過了廣告、社羣與硬件的總和。
直到 2017 年 3 月,蜻蜓才全面進入知識付費領域,緊接着,蜻蜓推出了高曉松的付費節目《矮大緊指北》,一個月付費用户超十萬,總收入超兩千萬。區別於喜馬拉雅 “乾貨型” 內容,蜻蜓的知識付費產品偏人文基調。
推進知識付費後,蜻蜓 FM 很快迎來了投資。2017 年 9 月,蜻蜓 FM 獲得百度和微影資本領投的 10 億元融資,創下了移動音頻行業單輪融資記錄。對這輪融資,彼時新任蜻蜓 FM CEO 鍾文明將其歸因於知識付費打開了音頻行業天花板。
荔枝 FM 有意放棄了整個知識付費的紅利,與曾經廝殺在一起的移動音頻平台分道揚鑣。2017 年 10 月,荔枝推出音頻直播功能,上線三個月,荔枝直播業務的營收超過千萬。到 2018 年 1 月,荔枝的語音直播打賞月流水超過一億,成為主要收入來源。
避開音頻行業主流競爭的荔枝,開始憑藉音頻直播和語音互動打造聲音互動社區,其特色是產品年輕化程度極高,超過 80% 的用户是 90 後和 95 後。
荔枝 FM 創始人賴奕龍曾提到,荔枝不做知識付費的理由在於荔枝 FM 一直在做 UGC,平台互動性也比較強,如果做 PGC 知識付費其實是進入到自己最弱的一塊。而荔枝從來不把主流移動音頻平台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年輕人社交才是荔枝關注的競爭領域。
這邊,喜馬拉雅意圖打造大而全的知識類淘寶天貓,一舉向大規模和大用户進軍,但此時,知識付費的熱潮正在退卻。
一位曾經的喜馬拉雅用户唐勤告訴奇偶派,在讀研究生的她,現在已經不怎麼喜歡聽知識付費類的音頻了,2018 年左右,她還在本科學財務,當時一門財務課的老師推薦了喜馬拉雅上的一門財務課程,愛學習的她便下載了這款軟件,關注了一攬子財經頻道,但後來她發現,自己聽的時間並不長,只有晚上跑步或者做一些雜事的時候聽一聽,聽的最多的反而是一些新聞和故事,比如《吳曉波頻道》和《美麗説》,前者講財經新聞,後者講社會的一些奇葩故事。
現在,唐勤已經卸載了這款軟件,她説,雖然欄目挺多的,但是想要找到一個 “語言生動,沒那麼死板” 的課程還是需要花不少時間,而不喜歡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實是不怎麼有聽的習慣,不感興趣的原因也有,覺得該聽,但不想聽。”
音頻知識付費看起來像是個偽命題,餘建軍曾提到,喜馬拉雅在音頻行業佔有率超 7 成,但整個人羣滲透率只在 20% 到 30%,知識付費已經無法滿足音頻平台對用户與付費增長的雙需求。2018 年,喜馬拉雅將 123 的 “知識狂歡節” 改為 “狂歡節”。
在知識付費的生態發展邏輯裏,知識付費的獨立性遠高於音頻平台,當知識付費的教育屬性越大,音頻與教育的可剝離度就越高,這背後反映出,知識付費不是獨生於音頻平台的機會,它只是一個表現載體,用音頻做知識付費,必然走向終結。
於是,我們看到了羅振宇和他的得到 APP,樊登和他的讀書會,這些兼具個人 IP 的音頻內容,效率極高且具有層級分明的分銷體系。而這些平台,更像是一個教育學習平台,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音頻平台。
唐勤也提到,她雖然最先下載的是喜馬拉雅,但並沒有在上面花一分錢,反而是在得到上買過薛兆豐的課。
2018 年之後,知識付費的風潮在音頻行業正式散去,一級市場活躍度降低,廣義用户上的知識焦慮和消費興趣都開始下降。
從搬運式的場景更替到可剝離的知識付費,8 年下來,移動音頻行業只走出了一個差異化競爭的荔枝,而如今,荔枝也面臨着增長和單一模式的瓶頸,而主流賽道上的引領者如喜馬拉雅和蜻蜓 FM,還沒有找到真正屬於聲音的內生價值,在這場用聲音廝殺的賽場上,看似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實際上卻是封閉無聲的。
03
巨頭入場,蛋糕能做大?
長期以來,音頻行業承受着不少質疑,商業模式變現力弱、內容生態是否具備護城河、資本對耳朵經濟的低感知,這些也都是行業內幾家頭部公司的隱痛。那麼,聲音的內生價值到底在哪裏?
像尋寶遊戲一樣,喜馬拉雅繼知識付費之後有了一個新的結論,下一個增長點是有聲書和廣播劇。2018 年 9 月,在喜馬拉雅 FM,有聲書部分為平台貢獻了超過一半的流量,收聽時長佔比超過 60%。
有聲書和廣播劇,這些泛娛樂化的付費產品,淡化了此前知識付費產品的教育屬性,這類自制音頻內容對原著的保持程度高,成本較低,這似乎更適合音頻這種媒介。
從內向外看,這具有理論上的價值。於平台自身而言,它提升了自身的豐富性和內容壁壘,對外界而言,這類長音頻產品耗時長,在整體互聯網中,時長代表着用户粘性和流量,反過來,長音頻可以提升音頻平台價值,助其開疆拓土。
很快,各大音頻平台視長音頻為有內生力的全新賽道,有聲書、廣播劇、相聲、脱口秀等在內的多個聲音品類相繼被音頻平台納入內容整體版圖。

2019 年 12 月,喜馬拉雅推出千萬級製作的超大 IP 廣播劇《三體》;蜻蜓 FM 也收縮對 “知識付費” 的戰略承諾,轉向推動優質內容付費,相繼推出 91 傾聽日、超級會員等活動,提出有聲書精品化戰略。
泛娛樂化 IP 的音頻化改造,起到了一定的效益。2020 年,喜馬拉雅用户突破 6 億,比去年同期增長 1.2 億,其中 90 後用户在半年內增加了 36%。
很快迎來新的進入者。從場景到付費到 IP,音頻行業埋頭尋路十年,而移動互聯網的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短視頻平台崛地而起,成為新的時間殺手,音樂巨頭 TME(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感到了增量焦慮,2020 年 4 月,TME 發佈長音頻 APP“酷我暢聽”,長音頻作為 TME 集團戰略被提出。這項戰略也獲得了閲文集團的支持。
就在酷我推出自己的長音頻之後兩個月,字節跳動推出有聲閲讀平台 “番茄暢聽”,與自身網文平台 “番茄文學” 相互配合。
音頻老廠牌和自帶流量資源的巨頭戰略性交叉,音頻行業將如何變革?
騰訊音樂娛樂集團酷我音樂副總裁肖軼認為,只有在業態上創新,打造出破圈的創新產品,從根本上提高行業滲透率,才有希望看到在眼球經濟籠罩之下的時代,耳朵經濟有機會靠近主流。
而音頻行業的有聲廣播劇其實是視聽行業最低的一個門檻。除了沒有畫面,所有的聲效、表演一應俱全,他認為,這是 IP 產業鏈試錯最好的方法,“但是目前我們仍然面臨這麼大的一個轉換漏斗。”
這看起來是要從上至下完善生態鏈條?TME 給出的解法是,“音頻的可視化”。例如,音頻行業中最核心的一個品類叫做 “有聲閲讀”,這可以讓音頻可視化,在這種模式下,用户可以不停腦補這個場景,甚至回憶這個場景,甚至和人互動。
在產品層面,TME 除了推出的長音頻全新產品 “酷我暢聽”,QQ 音樂在 2020 年 12 月接入中文播客產品 “小宇宙”,在一級頁面上線 “播客” 獨立模塊,酷狗音樂推出長音頻產品"酷狗聽書",並上線"劇場"功能,在常規聽覺產品中加入視覺元素,推動長音頻進入可視化時代。
在內容層面,TME 與閲文等平台戰略合作,新增數千本有聲讀物內容,獲得多部作品的音頻作品改編權。除在線文學作品之外,還開始與熱門電視劇以及國內漫畫 IP 合作進行音頻化改編。
今年 1 月 23 日,TME 收購了音頻平台 “懶人聽書” 100% 股權,進一步加碼長音頻的相關資源佈局。TME 發佈的最新財報顯示,四季度 TME 平台長音頻專輯數量同比增長 370%,長音頻 MAU 滲透率從去年同期的 5.5%增長至 14.8%。
在 TME 的一連串動作中,可以看到,TME 的 “音頻可視化” 之路關鍵在於自產、合作相關音頻產品,以及包攬相關內容產品的改編權,但這對最初提到的 “業態創新、打造出破圈的創新產品” 到底有沒有更長遠的幫助?
在 TME 力推的長音頻產品 “酷我暢聽” 綜合搜索榜上,奇偶派看到,排名前十的作品中,有 7 部作品來自影視文學類幾乎已經破圈的作品,排名前三的為《盜墓筆記》、《趙本山小品》、《山河令結局》。
一位酷我暢聽用户表示,“別的不説,就衝酷我暢聽有《我愛我家》和脱口秀,這款 APP 在我心中就是第一。” 還有用户告訴奇偶派,最近兩年的廣播劇太多了,貓耳、網易雲、克拉克拉、喜馬拉雅這些平台都在製作廣播劇,競爭很激烈,酷我暢聽毫無存在感,“這個平台很冷。”
對於用户而言,平台對他們的吸引力並不取決於平台本身,而在於平台播放的作品,用户跟着熱播作品走,而這些作品,本身並不是依靠這些音頻平台而走紅的。
這個問題,蜻蜓 FM 已經意識到。
2 月底,蜻蜓 FM COO 王磊就曾提到,過去行業中常提的爆款指的是賣得最多的內容,更多是基於銷量去定義,比如銷售量在千萬以上、3000 萬等等。但實際上,音頻內容長期由視頻內容、評書作品、閲讀作品等中轉錄而來。
過去我們更多是拿來主義做法,好處是這很快速,不需要對內容進行打磨,弊端是久而久之對上游養成了長久依賴,這個東西做到極致,其實還是在為兩邊去打工。我們需要做一個音頻驅動的,由音頻打造爆款,再複製到其他媒體類型的絕對意義上的爆款。
TME 和蜻蜓都發現,瓶頸卡在內容供給裏,大部分音頻的紅利和內容不是來自於音頻原創,而是對已有成熟的其他內容媒體類型的遷移。
答案昭然若揭。
音頻佔據用户的時長確實很長,但即便有巨頭青睞,音頻經濟歸根結底還是一門不好做的生意,從上游的內容獲取、到下游的內容分發,關於聲音這一載體所依賴的整個生態鏈條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發展。
巨頭入局,做的還是老式音頻平台一直在做的搬運工作,這並不能做大行業蛋糕,找到聲音的內生價值、完善生態鏈條,依然是根本。
04
變與不變,音頻難出圈
斷裂的生態鏈,讓聲音的價值藏在隱秘的角落,疫情卻像是套全新的編譯系統,喚醒了聲音領域一個 “古早物種”——播客,這個完全由主播原創,並以長音頻為媒介傳播的內容形式,在 2020 年呈現燎原之勢。
播客搜索引擎 ListenNotes 的數據顯示,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國大陸播客的數量為 16448 個。這個數字在 2020 年 4 月底時剛剛突破 10000 個,僅 2020 年後三個季度,中國大陸播客新增 6539 檔。據國內播客應用 Moon FM 的數據顯示,2020 年新增中文播客 6569 檔。這一數字超過了過去五年新增中文播客數的總和(6380 檔)。

這是繼音頻知識付費後,聲音內容領域又一次多家頭部平台參與的罕見熱潮。2020 年 3 月,即刻團隊推出的國內首個獨立播客 App 小宇宙,這攪動了行業的那條鯰魚,也徹底帶動了播客這波風潮。
這些短則 1 小時,長則 2~3 小時的長音頻,相比 IP 類音頻內容,更具有靈活性和真實感
,這些 UGC 感較強的主播級內容,在整個音頻生態裏建立起了內容與聽眾之間的特殊聯繫。
而這種特殊聯繫是有跡可循的,小宇宙由擅長圈子型社區的即刻團隊孵化而出,這側面證明了播客的圈子屬性,而這種圈子式聚集往往是出於聽眾對主播及其內容的認同和好感而產生的。
播客愛好者沈貝貝告訴奇偶派,在播客集中爆發之前,2018 年 11 月,機緣巧合下,她愛上了聽播客,彼時還沒有出現小宇宙這樣去中心化的內容推薦機制的播客平台,“主播就把節目放在網易雲上,每期節目時長都很長,最長的能長到 5 個小時,但我會一期不落地全部聽完,特別喜歡的幾期還會反覆收聽。”
跑步、上下班、做飯,在做雜事的時候,收聽播客已經成為她生活中的一種習慣,久而久之,沈貝貝會對主播越來越熟悉,“除了他們談論的內容,就聽他們説話的節奏、語調,你就能判斷出他們是一怎樣的人,慢慢地會產生很強烈的信任感,就像你的朋友一樣。” 沈貝貝形容這種沉浸式的體驗,像一場漫長的、滲透式的、用耳朵參與的 “聲音真人秀”。
收聽播客時,沈貝貝並不會主動去想象主播們圍繞在一起錄製的畫面,沈貝貝認為,想象畫面是一種破壞,“我只對他們的聲音和內容感興趣。” 最近兩年,播客幾乎佔據了她大部分閒暇時間,為此,她放棄了曾經看電視劇的消遣方式,“聽播客和追劇差不離,輕鬆還有趣,太長了就分期聽。”
奇偶派瞭解到,大部分聽眾都是去年發現的播客,他們基本都在通勤時聽,“地鐵太擠,連刷手機都覺得費勁,更不用説看書了。而戴耳機就方便多了,從家到公司 1 小時,播客大都 1 小時左右,時間正好,內容輕鬆但又有內容。”

對音頻平台來説,播客屬於最典型也是最優質的小社羣案例,類似於視頻世界的 vlog 等中視頻,在自己的內容品類之中屬於質量升級的產品,也有着較好的口碑性訂閲。
在經歷了知識付費的慘淡收場後,音頻平台們在內容選擇上也變得更多元,音頻行業的故事又繞回了曾經不起眼的播客,但這像是能解燃眉之急的 “新泉水”。跟隨者眾,在音頻、音樂等行業,各家紛紛下場。
喜馬拉雅增設獨立播客頻道,網易雲音樂電台入口更名為 “播客”,QQ 音樂首次增設播客 Tab 接入小宇宙,快手和荔枝 FM 先後推出獨立播 App,甚至 TME 內部因為播客一事還搞起了內部賽馬。
有喜馬拉雅內部人士曾表示,平台之所以接納播客,是因為播客內容足夠真實和多樣化,且具備長尾效應、粘性更高。而通過扶持播客,一定程度上可以豐富、完善喜馬拉雅的內容生態。
而對大部分主播而言,他們大部分是入不敷出的,除了口播廣告,還沒有更合理的商業模式出現。在美國,每 1000 次播放量可以為播客帶來 20 到 100 美元的廣告收入。但在國內,這一收入要低得多。
聲動活潑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丁教就曾表示,目前與品牌商的廣告合作,平均播客水平 CPM(每千次展示費用)為 6 毛錢到 7 毛錢,按最終收聽人次計算。
《隨機波動》主播則透露,他們的 “播客事業” 依然還需要靠家裏支持,有的時間不得不接幾篇軟文,但要知道他們已經是小宇宙上訂閲量最高的播客之一。
沈貝貝也提到,她收聽的大部分播客現在都 “用愛發電”,她很希望自己喜歡的播客能夠 “做大做強” 活下來。
而過去 2 年,活得比較好的,例如,JustPod(一家本土播客製作公司,旗下擁有忽左忽右等多檔原創播客),他們養活自己的方式是為多個企業客户製作播客,據楊一介紹,製作費用通常是談話類節目 2w/集,敍事類型的 6w/集,這也是他們現在最大的收入來源。
對主播們來説,做播客其實不賺錢,長期以來,他們不受廣告主的待見,而這背後還是行業鏈條的缺失,體現在數據端統計困難。
在國內,播客的分發形式主要還是 RSS( 這是蘋果建立並改進的播客格式標準,聽眾可通過 RSS 地址獲取節目,符合協議標準的泛用型客户端都可以通過 RSS 地址來抓取節目),雖然部分音頻平台有收聽量統計,但國內播客 50% 的流量都散落在泛用型客户端(比如蘋果播客、小宇宙)上,因為統計口徑不一,這讓收聽量統計變得困難。
《三好壞男孩》主播大腸認為,從目前來看,如何將全網數據打通,國內還沒有一家平台可以做到,而沒有數據反饋,廣告主的態度一定是謹慎的。
大腸不承認播客是一個行業,“一個行業應該有完整的上中下游,有供應商、研究機構、行業媒體和行業組織。但這些,中文播客幾乎都沒有。”
對於播客來説,其已經具備了獨屬於聲音的內生價值,符合互聯網的某些特質,比如感人的時長、忠實的聽眾、社羣的屬性、多元化的內容等,而這些特質,極有可能顛覆傳統音頻平台的運營模式。
但無論小宇宙、荔枝、快手推出的獨立播客 App,還是喜馬拉雅完善自身平台內容的參與式態度,播客都被當作是創業公司的創業產品或項目,沒有哪家平台願意梳理清楚背後的運營邏輯,歸根到底,這還是囿於一種結構性困境,音頻或者播客,無法擁有完整的產業鏈條。
聲音,這種古老的媒介,始終未曾改變,而在如今的互聯網商業環境下,它來回的變動,卻始終沒辦法出圈,也註定不能出圈。
05
寫在最後
互聯網發展得太快了,一下子從圖文衝到了視頻,沒有給音頻機會,有聲音這樣總結音頻行業的失敗。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回溯音頻十年,從流量到資本到風口,音頻行業統統都擁有過,但十年過去,我們看到,音頻行業仍像在玩尋寶遊戲一樣,尋找着真正屬於聲音的價值。
但現實是,當真正有價值的音頻形態復甦而不是出現,且正有破圈之勢時,卻遺憾沒有能落地發芽的土壤。
或許靶子一開始就是打歪的,如果説最開始為了瓜分市場份額,複製粘貼式的場景更替不可避免,那在知識付費的風潮退卻之後,各大音頻平台還是有機會去梳理音頻行業的底商業邏輯的。
做《忽左忽右》已近 3 年的楊一説,“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十年前,你或許讀到了一本《尋路中國》,你發現原來特稿與非虛構故事還可以這麼寫。但聲音呢?我們在中文語境對於 ‘人類對聲音媒介的可能性挖掘到了什麼程度’ 瞭解得似乎太少了。”
現實看來,中文播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靠等靠要的搬運工——音頻平台們,或許註定只能圈地自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