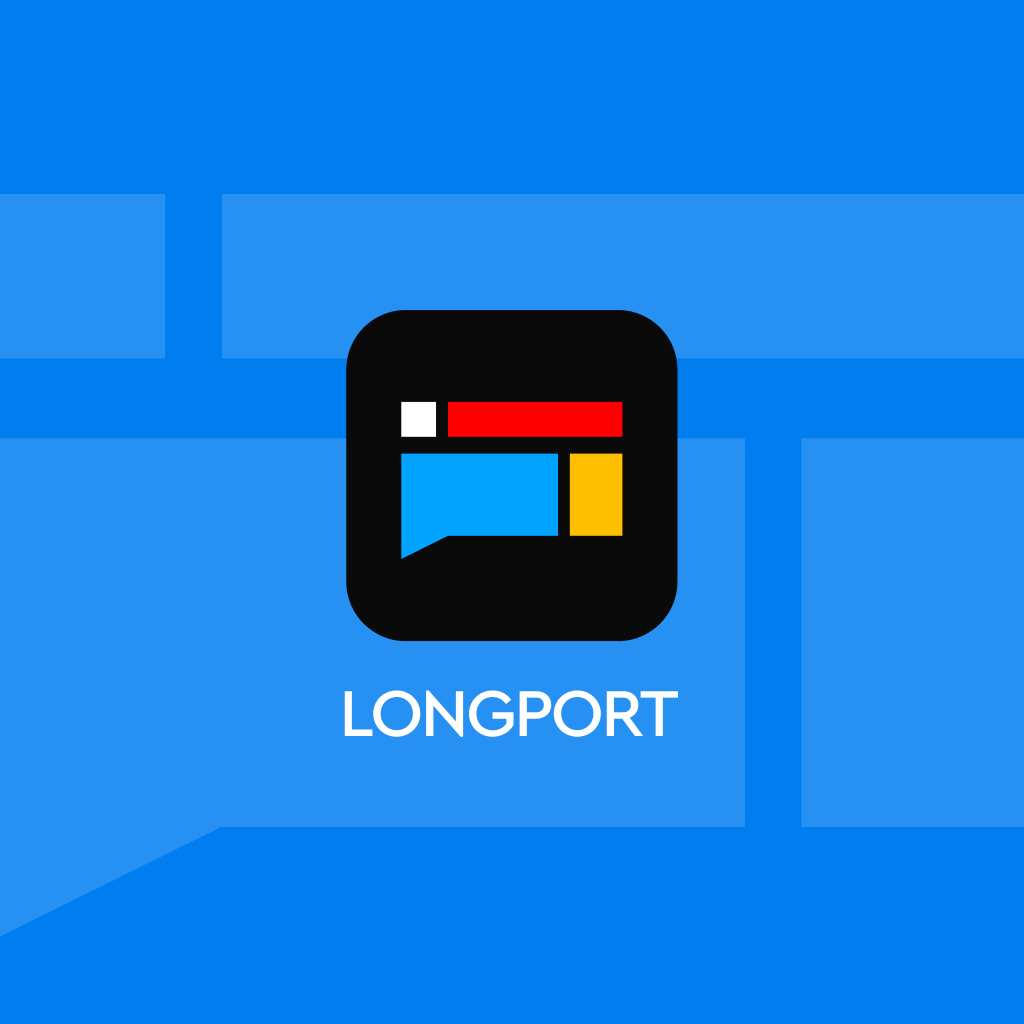
加息下狠手,美聯儲 1994 的未解之謎

1994 年的特殊之處在於激進加息下經濟實現了少見的軟着陸,美元指數持續貶值,以及美債收益率階段性見頂。
加息和縮表不斷提速,美聯儲官員近期頻頻援引 1994 年作為本輪緊縮週期的參考對象。2022 年 3 月美聯儲首次加息以來,市場對年內的加息預期已經超過 200bp,自 1990s 以來僅有 1994 年的加息達到類似的幅度(250bp)(圖 1),而1994 年的特殊之處在於激進加息下經濟實現了少見的軟着陸。
除此之外,從主要資產的表現來看,2022 年和 1994 年確實存在不少相似之處(圖 2),但美元指數的表現卻大相徑庭,2022 年第一季度美元指數已升值 3%,但 1994 年全年美元貶值超過 8%。而觀察當年債市的表現,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在經歷年初的大漲之後,5 月至 9 月基本保持震盪,而同期美聯儲加息 100bp。
我們將上述的 “經濟軟着陸”,“美元大貶值” 和 “加息債不跌” 稱為 1994 年的三大謎題。我們試着從這三大謎題,分析 2022 年和 1994 年的異同,尋找政策和資產變化的蛛絲馬跡。
謎題一:“經濟軟着陸”
按住通脹的苗頭,“前瞻式加息” 是重要基礎。經歷了 20 世紀 80 年代沃爾克治理通脹的時期後,1994 年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十分重視通脹,採取的是 “前瞻式加息” 的框架,在產出缺口尚未轉正,通脹壓力出現苗頭的情況下果斷加息。這樣的好處是經濟在動能和空間上都有較好的緩衝墊(圖 3)。
貨幣政策足夠靈活,該降息時果斷降息。1994 年 2 月美聯儲首次加息,1995 年 2 月最後一次加息(50bp),之後三週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聽證時即暗示可能會對經濟衰退做出提前反映。並於 1995 年 7 月和 1996 年 1 月分別進行了 2 次預防式降息(而不是等到衰退出現)。
運氣同樣重要,外部環境穩定是美聯儲 “精準調控” 的重要保障。1994 年德國、日本走出衰退,全球共振復甦;主要國家達成多邊貿易協定,WTO 即將成立;俄羅斯仍在親英美的葉利欽治下;油價最大漲幅 47%,全年漲幅 25%,尚屬可控。正如前美聯儲主席耶倫在書中所説:
雖然美聯儲的政策轉換的巧妙性是毫無疑問的,但美聯儲也很幸運,1994 年至 1995 年間,沒有任何重大沖擊來破壞它試圖實現的經濟軟着陸。
形似而已,本輪美國要實現激進緊縮下的 “經濟軟着陸” 的難度很大。如圖 4 所示,本輪美聯儲加息已經失去了 “先手優勢”,產出缺口轉正意味着美聯儲加息是滯後的,在這種條件下緊縮帶來的金融條件收緊將對經濟動能產生明顯的副作用(圖 4 和 5),而這種跡象在美國 PMI 的數據上已有體現(圖 6 和 7)
除此之外,外部環境上中歐經濟尚未企穩,疫情和地緣政治衝擊不斷,無疑將使得美聯儲調控經濟和通脹的難度大大上升。展望未來,美聯儲可能不得不在比計劃更早轉向寬鬆,和用衰退治理通脹之間做出權衡。這也將考驗白宮是否有勇氣用一場經濟衰退來迎接 2024 年的總統大選。
謎題二:“美元大貶值”
1994 年美聯儲激進加息下美元指數為何持續貶值?這可能是當年美國乃至全球核心資產表現中最大的謎題。
無論從貨幣政策,利差還是資金流動等常見角度都無法解釋 1994 年美元的弱勢。1994 年 2 月美聯儲開啓加息(直至 1995 年 2 月),同期德國和日本都處於降息週期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和其他主要發達經濟(以德日英為代表)之間的長短端利差震盪走闊,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明顯下降,甚至出現一定的負相關。跨境資金流動上,除年初外,1994 年外國投資在持續增配美國資產(尤其是美債),美國投資者則在持續減持海外資產,由此導致的資金淨流入同樣不構成美元貶值的基礎(圖 8 至 11)。
我們發現以上三個方面其實本質上都是從資本套利、資金流動的角度去判斷匯率,即資金傾向於流向高息資產,推升相關貨幣的匯率。但是除此之外,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扮演者重要的中介角色,它的特殊性在於美元匯率還是全球經濟和貿易的温度計,即全球經濟復甦和貿易擴張往往對應着美元貶值。
1994 年以德國和日本代表的全球共振復甦是美元走弱的重要驅動力。20 世紀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德、日的加息週期導致歐洲貨幣危機(例如 1992 年索羅斯突襲英鎊)和日本資產泡沫的破裂,1993 年德國和日本雙雙跌入負增長。不過,1994 年全球經濟和貿易觸底明顯反彈,一方面德日經濟共振復甦託底全球經濟;另一方面,1994 年全球多邊貿易協定達成重要協議,1995 年 1 月世界貿易組織組織正式成立,全球化加速下全球貿易大幅擴張(圖 12)。
這一模式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即使美聯儲處於緊縮週期中,全球經濟復甦和貿易擴張也會導致美元表現偏弱,例如 2013 年和 2017 年(圖 13)。
進入 21 世紀,隨着中國納入全球貿易體系,中國逐步取代德日成為全球經濟的(非美)發動機,中國經濟成為美元指數走勢的前瞻性指標。如圖 12 所示,雖然人民幣並不在美元指數的貨幣籃子中,中國對美元的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全球非美經濟體增長的途徑:中國經濟復甦——拉動全球經濟復甦(我們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美元指數走弱(圖 14 和 15)。
上述邏輯和渠道的傳導存在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中國經濟的內生復甦企穩,二是中國經濟復甦能夠有效向全球傳導。而這兩點在 2022 年都面臨一定的約束。
以史為鑑,無論從政策、利差還是從全球經濟復甦的邏輯看,2022 年美元指數不會走 1994 年的老路,第二季度仍將保持相對強勢。從政策和利差來看美聯儲已經進入加速加息的週期,而受俄烏衝突的影響,歐央行仍保持謹慎,日本央行則繼續堅持控制長端國債收益率的政策,政策分化下美國與歐日的名義和實際利差都在走闊。
中國經濟不穩,俄烏衝突拉鋸是全球復甦 - 美元轉弱邏輯的核心賭點。2022 年以來國內穩增長的發力仍不足以對沖地產的疲軟,地產政策拐點向地產企穩的傳導仍需時間,疊加新一輪疫情爆發的影響,中國經濟在第二季度將二次觸底。俄烏衝突拉鋸和持續發酵帶來的大宗商品產衝擊、金融市場動盪以及地緣政治緊張都將成為全球經濟共振復甦的重要阻礙。
我們認為 2022 年第二季度美元指數將階段性站上 100。除了以上利多美元的因素外,第二季度美聯儲縮表的預期和落地會給美元指數火上澆油,美元指數將階段性站上 100。不過我們預計 2022 年第二季度末以及下半年,隨着中國經濟出現更多積極信號,以及俄烏衝突的負面影響邊際減弱,美元指數將出現回落。
謎團三:“加息債不跌”
起跑階段預期不足,加息之後預期過度。1994 年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聯儲在決策和市場溝通方面的透明度不足,遠不及伯南克、耶倫等繼任者。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在加息開始前,市場預期明顯不足,而美聯儲連續加息之後市場預期出現 “矯枉過正”,5 月議息會議前市場已經預期年內加息超過 170bp,而截至 1994 年 9 月,美聯儲實際加息 175bp。這使得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在 5 月至 9 月之間停滯不前(圖 16)。
2022 年市場搶跑明顯,1994 年重演的概率不小。與 1994 年不同的是當前美聯儲的溝通透明度已經極大改善,而這導致市場預期的搶跑十分明顯,美聯儲 3 月才加息 25bp,市場已經定價年內加息接近 250bp,過於激進的市場預期直接導致美債收益率出現了長短端倒掛。這明顯是不可持續的(圖 17)。
縮表衝擊後,美債收益率將階段性見頂。除了加息外,2022 年美債上漲的燃料還有縮表,而 4 月初以來 10 年期美債的繼續上漲,正是對激進縮表的定價——5 月開啓,每月可能縮表 950 億美元,縮表節奏比上一輪更快。縮表落定之後,10 年期美債收益率繼續上漲的動力可能不足,將陷入 1994 年年中相仿的震盪行情。
本文作者:陶川、邵翔,來源:東吳證券,原文標題:《加息下狠手,美聯儲 1994 的未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