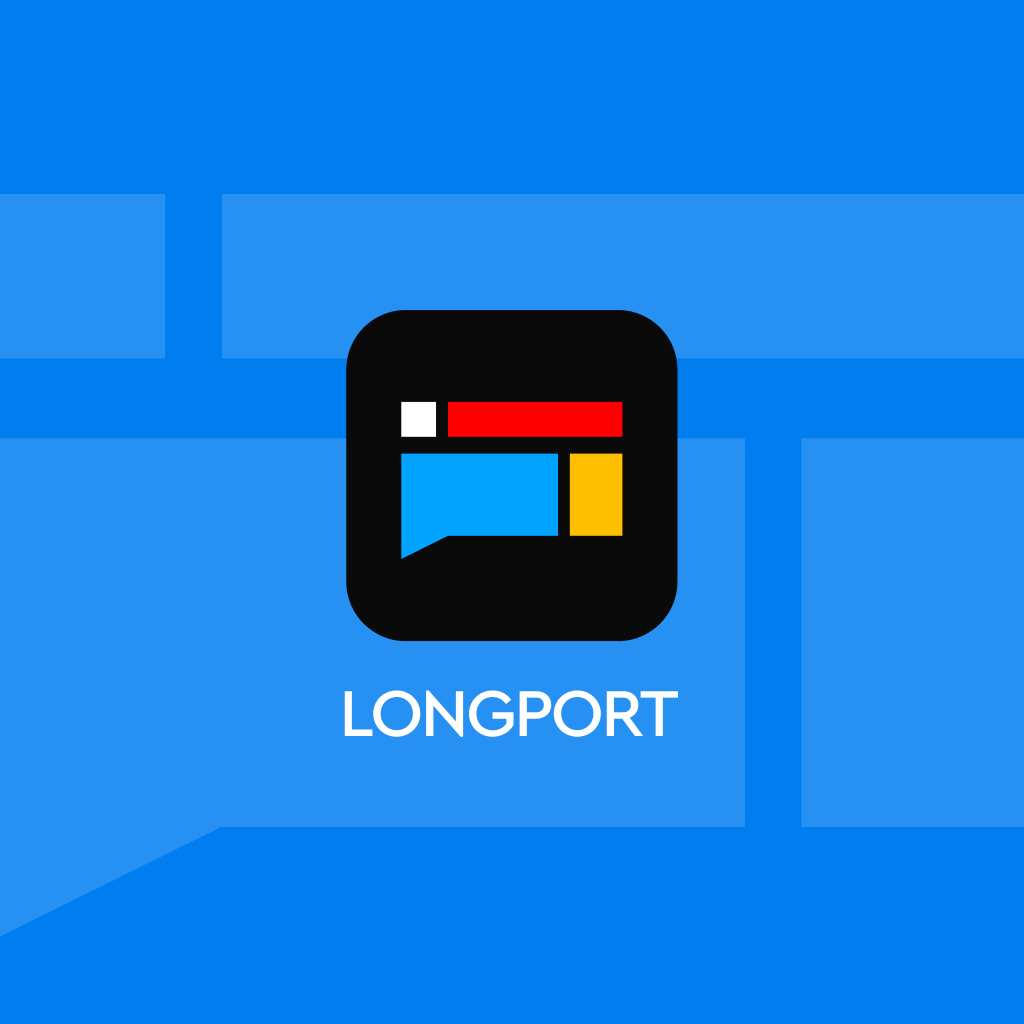
腹中的国运:儿时回忆的打虫糖,你真的了解吗?(上)

大家好,我是杰克。
我正在做一件笨事:按成立顺序,写完标普 500 的企业。
乔布斯曾说:“最终,一切都关乎品味。”
在投资世界中,这种品味首先指向看懂商业模式的能力。正如巴菲特强调,评价一家企业,必须从商业模式开始。唯有真正 “看过”,才能感知何为卓越。
巴菲特践行的方法极为朴素:翻开每一页。他曾两遍通读数千页的《穆迪手册》,不放过任何角落。芒格惊讶于他对加州小公司的熟悉,答案依然是——他早已 “翻开过那一页”。
我们从标普 500 开始。翻开每一页,是品味建立的第一步。
这是一场关于 “价值” 的长跑,一段认知不断前行的跋涉。是寻找同类的相互辨认,更是从孤灯前行到星河共亮的奔赴。
建议先关注,再阅读,我们一起深入。
-正文-
导读:本文以 “宝塔糖” 为切入点,通过回顾这一国民级驱虫药的兴衰,揭示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的艰难历程。文章剥离怀旧滤镜,通过山道年(Santonin)的引进、本土化及最终被更先进药物替代的历史,阐述了现代公共卫生建立在化学工业基础之上的冷峻事实。这不仅是 “打虫药” 的进化,更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近现代医药工业史。
前一阵社交媒体上又掀起了一股怀旧风。
有人晒出了小时候吃过的 “宝塔糖”,那些五颜六色的、棱角分明的圆锥体,立刻引发了 70 后、80 后甚至部分 90 后的集体共鸣。
评论区里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回忆:“那是童年最甜的记忆”、“现在的药没有以前那个味儿了”、“那是我们回不去的纯真年代”。

每当看到这种对匮乏年代的盲目美化,我就不得不站出来泼一盆冷水。
今天,我们要剥开这层温情脉脉的糖衣,看一看包裹在里面的残酷真相。我们要讲的,不是一个关于童年味蕾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 “落后农业国” 如何通过工业化手段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
这颗糖的兴起与消失,恰恰证明了一个观点:现代生活是脆弱的,也是昂贵的,它建立在对自然界的残酷征服和对落后生活方式的彻底背叛之上。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卫这种背叛。
对于 1990 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关于 “寄生虫” 的记忆是苍白且无菌的。
那大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两片白色的药片(阿苯达唑)被随手丢进嘴里。有点甜,像奶糖。吃下去之后,什么也不会发生。肚子里的蛔虫、钩虫、蛲虫,在不知不觉中被阻断了葡萄糖摄入,饥饿至死,溶解成水,消失在现代化的抽水马桶里。
还有些 90 后小伙伴可能想到了 “糖丸”,但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小时候打针时,医生常用一颗甜甜的 “糖丸” 安抚我们,其实那是预防小儿麻痹的脊灰疫苗。顾方舟发明的这种疫苗,利用减毒病毒与辅料做成口服形式,拯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如今疫苗已改为注射和口服滴剂,程序更加科学,但 “糖丸” 仍是许多人心中的记忆。

但对于 70 后和 80 后而言,打虫是一场充满血 腥味与仪式感的集体童年回忆。
记忆的载体是那座五颜六色的 “宝塔”。粉红的、淡黄的,棱角分明,像是一个微缩的建筑模型。

吃下它的第二天是惊心动魄的。在遍布苍蝇的旱厕边,孩子紧张地盯着下方。直到看见那条长约 20 厘米、粉红色、还在蜿蜒扭动的蛔虫被完整排出,一种混合了恐惧与成就感的战栗才会传遍全身。

这种 “看得见” 的疗效,曾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理慰藉。
然而,1982 年 9 月,卫生部一纸公文,宣布淘汰 127 种药品,“宝塔糖” 的核心成分——山道年(Santonin)赫然在列。随后,曾被视为国家机密的制药原料——蛔蒿,在中国大地上基本灭绝。
所以,很多 80 后小时候吃的宝塔糖,其实已经是 “挂羊头卖狗肉” 了——外形还是宝塔,但里面的成分已经换成了更便宜、更稳定的磷酸哌嗪。
为什么一种用了上百年的神药会被禁?为什么一种植物的成分提取会牵动中苏两国的冷战神经?
当我们剥开这颗糖衣,里面包裹的不仅仅是药粉,而是一部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百年激荡史。
01 晚清:四万万 “腹中之国”
现在很多人反感现代化工,推崇 “纯天然”、“有机”、“古法”。在他们的想象中,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农村,是山清水秀、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
如果你真穿越回去,哪怕只是回到 19 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迎接你的不是诗和远方,而是粪便和寄生虫。
19 世纪末的中国农村,是一幅病理学的浮世绘。
一位在四川行医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儿童普遍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体态——四肢如枯枝般纤细,面色蜡黄如土,但腹部却异常鼓胀,如同怀胎十月的妇人。”
这并非简单的营养不良,而是重度寄生虫感染的典型体征——“虫积”。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前工业时代农业社会的必然诅咒。
在那个没有化肥的年代,人畜粪便是最珍贵的肥料。农民将新鲜的粪便泼洒在菜地里,蛔虫卵附着在青菜叶上。简单的清洗无法去除具有黏性的虫卵,甚至很多贫苦人家有喝生水的习惯。
一个生活在晚清或民国农村的普通人,他的一生就是和寄生虫共生的一生。
虫卵入腹,在小肠孵化,幼虫穿破肠壁进入血液,流经肝脏、心脏,最后到达肺部,再顺着气管爬到咽喉,被吞咽回小肠发育成成虫。

这一条完美的闭环,在四万万中国人的身体里周而复始。据 1930 年代的一项公共卫生调查推测,当时中国农村人口的蛔虫感染率高达 80% 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 95%。
一个面黄肌瘦的壮劳力,肚子里可能养着半斤重的虫子。它们争夺着宿主仅有的一点口粮,分泌毒素影响智力发育。
也就是说,当时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行走的虫巢。
面对这种大规模的生物寄生,我们的传统医学表现如何?
很遗憾,在以解剖学和微生物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降临之前,传统医学是无力的。
中医古籍称之为 “蛟龙” 或 “长虫”。《本草纲目》记载了使君子、乌梅丸、苦楝皮等方剂。
使君子确实有效,但毒性难控。吃少了没用,吃多了会导致严重的呃逆(打嗝不止)和呕吐。苦楝皮则更为猛烈,过量服用会导致胃出血甚至肝肾衰竭。
在没有现代萃取技术和定量分析的古代,医生开药全凭经验,这就是在拿人命赌博。
在正规中医之外,广大的乡野滑向了巫术的深渊。
道教将寄生虫神魔化为 “三尸虫”。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孩子肚子痛(蛔虫钻胆),父母往往不去药铺,而是去庙里求一张黄纸符,烧成灰,兑水灌下去。
更惨烈的是 “以毒攻毒”。在晚清的《申报》角落里,时常能看到儿童因吞食水银、雷公藤而中毒身亡的惨案。父母并非不爱孩子,而是在看着孩子痛得满地打滚时,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 “雷霆手段”。
所以,不要美化 “古法”。在工业化学品阿苯达唑(肠虫清)普及之前,中国人的肠道控制权,从来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在寄生虫手里。

100 多年前,是谁打破了这个僵局?
是化学。
19 世纪中叶,西方从植物 “蛔蒿” 中提取出了山道年(Santonin)。这是人类第一种像样的驱虫药。
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山道年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买办经济痛史。
山道年提取自一种生长在北极圈附近的植物——蛔蒿(Artemisia cina)。
在 19 世纪末,全球的化工霸主是德国。生产山道年需要掌握有机化学提取、结晶和纯化工艺,德国的默克(Merck)和拜耳(Bayer)几乎垄断了这种药物的生产。
在上海著名的屈臣氏大药房(A.S. Watson & Co.)里,深棕色玻璃瓶装的德国原装山道年,晶莹剔透,纯度极高。

但它太贵了。
根据 1910 年的物价,一盎司(约 28 克)德国山道年粉末,售价在 10 到 15 块银元之间波动。
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时,月薪也不过几百大洋;而一个拉黄包车的骆驼祥子,拼了命跑一个月,除去车份儿钱,剩下的只能勉强糊口。普通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可能都买不起这一小瓶药。
对于绝大多数晚清百姓来说,德国人的山道年,就像那大玻璃橱窗里的西洋自鸣钟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物。
他们只能继续给孩子灌符水,或者去买那些成分不明的江湖大力丸。
这就是前工业国的悲哀:你知道有药能救命,但你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你没有任何议价权。
02 商业天才与 “爱国神药” 的谎言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驱虫药很早就经历过一场 “口感革命”。
早在 1849 年,辉瑞公司(Pfizer)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埃尔哈特,利用他作为点心师的技能,将苦涩的山道年混入奶油太妃糖,用做蛋糕的裱花嘴挤出了圆锥体的形状。这就是后来 “宝塔糖” 的雏形——“山道年圆锥糖”。
但遗憾的是,晚清的中国孩子,注定尝不到辉瑞那口正宗的 “美式蛋白脆饼”。
这背后是地缘政治与物理天堑的双重壁垒。
首先是距离太过遥远。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辉瑞所在的纽约距离上海太过遥远。而以屈臣氏(A.S. Watson)为代表的英资洋行,牢牢把持着远东的医药渠道。在大英帝国的贸易网络里,商船从伦敦或汉堡出发,穿过苏伊士运河直抵上海,这条航线比美国航线更短、更稳。 因此,能摆进上海滩大药房玻璃柜台的,大多是英国的硬糖锭剂或德国的结晶粉末。

没错,屈臣氏很早就进入了中国
其次是工艺的硬伤。辉瑞发明的初版宝塔糖,本质上是一种 “蛋白脆饼”(Meringue)——用蛋白霜和糖浆打发,酥脆松软。这种娇气的 “法式甜点” 根本熬不过海上三个月的高温与颠簸。
相比之下,欧洲人出口到中国的往往是质地坚硬的糖果片,或者是直接出口原料。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掌控中国医药市场的洋行买办(Compradors)的算盘。对于屈臣氏大药房(A.S. Watson)或德国科发药房(Voelkel & Schroeder)的买办们来说,进口成品糖果是 “笨生意”。成品糖果体积大、易损坏、关税高,而且利润是透明的。
相比之下,进口德国默克(Merck)生产的高纯度 “山道年结晶粉末” 才是暴利。一小瓶晶体,漂洋过海运过来,买办们可以在后堂把它分装、稀释,甚至掺入滑石粉,调配成各种所谓的 “自制秘方”。
当时更普遍的情况是 “前店后厂”。像屈臣氏这样的巨头,往往会进口德国默克的高纯度原料,然后由自己的药剂师在上海或香港的工场里,模仿西洋模具,就地生产。这是那个买办时代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所以,晚清 “富家子弟” 吃到的 “洋行宝塔糖”,很可能是一颗流着德国血液(原料)、披着英国外衣(品牌)、却有着中国出生地(上海制造)的混血糖。
于是,晚清的驱虫药市场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分层:
顶层是德国货:深棕色玻璃瓶装的默克原厂结晶。纯度最高,价格最贵,通常只出现在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里。它是苦的,但那是 “尊贵的苦”。
中层是英国/本土改良货:像上海的爱儿康药房或英国药房,他们买来原料,自己在上海本地模仿辉瑞的工艺,现做现卖这种 “宝塔糖”。这属于那时的 “中产消费”,虽然不用忍受苦味,但价格依然不菲。

底层是日本货:一战后,日本化工崛起。日本的武田长兵卫商店(今武田制药)和盐野义,向中国倾销工业级山道年片剂。那是粗糙的、扁平的白色药片,极苦,杂质多,副作用大,但胜在极其便宜。对于广大吃不起糖塔的底层百姓,这是唯一的选择。
在清末民初,去屈臣氏大药房买一套正规的德国山道年疗程(药粉 + 蓖麻油/甘汞),最少需要 0.5 到 1 块银元。 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1 块银元,相当于一个壮劳力 20 到 30 天的全部工资,或者全家半个月的口粮。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花一个月伙食费去买几克洋药?那是天方夜谭。
一战后,日本趁德国战败,引进了蛔蒿种植(主要在朝鲜半岛和北海道地区),并由武田长兵卫商店(今武田制药)大规模生产廉价的山道年片剂。
日本人的倾销策略极其凶狠:降价。
到了 1920 年代,日本山道年片充斥中国市场。虽然便宜了,但中国老百姓依然不敢买。
原因有二:
第一,恐惧西药。当时的民间谣言认为西药是 “虎狼之药”,吃多了会绝后。事实上,山道年确实有副作用,会导致 “黄视症”(视神经中毒,看东西变黄)和惊厥。
第二,民族仇恨。五四运动后,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买日本药,就是给仇人送子弹。
市场呼唤一种既便宜、又安全、还爱国的驱虫药。
于是,民国医药史上一位 “聪明人”,“产品经理”——张思云,登场了。
张思云毕业于广东公医大学,是正经的西医科班出身。但他也是一位深谙人性的商业天才。
他敏锐地抓住了痛点:百姓信中医、恨日本、爱孩子。

1930 年代,他在上海创办宏兴制药社,推出了一款名为 “宏兴鹧鸪菜” 的产品。
这是一场利用信息差和民族情绪的商业收割。
我们来看看这款商业逻辑堪称完美的 “缝合怪”:
他从日本进口廉价、粗糙的工业山道年,磨成粉,掺入 90% 以上的面粉和糖。
然后,给它起个名字叫 “鹧鸪菜”(一种沿海红藻的名字,民间传说能驱虫),谎称是纯中药,是 “国货之光”。让老百姓一听就觉得亲切:“这是老祖宗的草药,不是洋人的毒药。” 实际上,药里根本没有一点红藻。
最后,在报纸上刊登 “胖娃娃” 的广告,甚至打出 “提倡国货,挽回利权” 的口号。

这就是民国工商业的底色。它没有建立自己的化工生产线,没有掌握原料的定价权。它唯一的 “创新”,就是把洋人的化学原料,包上一层 “中华传统文化” 的包装纸,然后利用同胞的爱国热情,赚取利润。
这叫什么?这叫买办资本主义。
直到解放后,新中 国政 府揭开了盖子,大家才发现:吃了十几年的 “海藻神药”,原来全是掺了面粉的日本化学粉。
张思云的营销手段,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让 4A 广告公司汗颜。
他在《申报》和《新闻报》上买下整版版面,一年广告费高达 25 万法币。
广告画面是一个巨大的、白白胖胖的婴儿。为了迎合当时人们对 “胖” 的极度渴望(胖代表健康、富足),这个婴儿往往只穿一个红肚 兜,甚至全 裸,展示着莲藕般的手臂和圆润的肚子。

对于那些看着自己孩子瘦骨嶙峋的父母来说,这个 “胖娃娃” 就是最极致的视觉诱 惑。
在南京夫子庙的宏兴分社门口,张思云安装了一个电动的机械小丑。小丑手里拿着瓶子,不停地做着喝酒的动作,周而复始。
这种西洋景让没见过世面的百姓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大家看稀奇的同时,也深深记住了 “宏兴鹧鸪菜” 这五个字。
最疯狂的是,宏兴甚至发行过一种带有软色 情意味的月份牌:画面是一个面对半 裸美 女 “坐怀不乱” 的小和尚,表现药力强劲。虽然这引发了卫道士的抨击,但争议本身就是流量。
靠着这种 “爱国 + 中医 + 疗效(其实是西药)” 的组合拳,鹧鸪菜在上海一年能卖出 1500 万包。张思云赚得盆满钵满,在香港盖起了 “鹧鸪大楼”。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用日本的原料,掺中国的面粉,喊爱国的口号,收割普通人的铜板。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卫生干部们接管城市后,很快发现了 “鹧鸪菜” 的秘密。化验单显示,这所谓的国药就是稀释的山道年。
按理说,这种欺诈行为应立即取缔。
但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缺药。
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进口山道年的渠道被彻底切断。如果取缔了鹧鸪菜,孩子们连这点稀释的药都没得吃了。
于是,上海卫生局只能采取一种务实的妥协:允许继续销售,但必须在包装上贴条,注明 “本品仅具驱虫功效”,不许再吹嘘能治百病。
这种妥协持续到了 1952 年。
那一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 “五 反” 运动(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张思云和他的宏兴制药社被作为 “奸商” 典型遭到了清算。罪名不仅是欺诈,更在于他利用人民的健康牟取暴利。
鹧鸪菜退场了,但几亿孩子的肚子还在疼。
谁来填补这个空白?
未完待续——秦王绕柱走
本文由普通网民以现代方法制作,Gemini 有巨大贡献。
参考资料: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十三辑(cssci 集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作者:周永生
杰克:这是我在为写作标普 500【8】辉瑞制药收集资料过程中,意外发现的一段故事。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受震撼,一花一世界,小小的线索是可以挖掘出一个很大天地的。为了可读性,我额外组织更多资料,写成本文。限于篇幅,将分段发表。在此先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让你多一个角度,看清了商业表象背后的真实肌理,欢迎点赞、在看、转发。
-END-
大家好,我是杰克。
我在按照成立时间顺序逐个写标普 500 的成分股公司。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因为时间是商业世界里最无情的审判官,也是最公正的加冕者。
在这个系列中,我将遵循 “林迪效应”(Lindy Effect)的指引——对于一些不会自然消亡的东西(比如技术、思想、公司),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未来能存在的时间往往也越长。
我们要拆解的,不是几根 K 线的涨跌,而是商业模式的 “骨骼” 与 “肌肉”。为此,我特意剔除了金融类(Financials)和公共事业类(Utilities)。
为什么?因为银行和保险的资产负债表往往像一个无法彻底看透的 “黑箱”,杠杆是它们的氧气,也是它们的毒药;而公共事业虽然稳健,但更多依赖特许经营权和监管红利,缺乏在自由市场搏杀出的野性。我们要寻找的,是那些在残酷的自由竞争中活下来的 “非金融实体”。
按照成立时间一家家写下去,我们将看到一幅壮阔的图景:
从 18 世纪的运河与面粉厂,到 19 世纪的铁路与钢铁,再到 20 世纪的消费品与石油,最后是 21 世纪的硅谷芯片。这不仅是一份标普 500 的名单,更是一部活着的资本主义进化史。
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将带大家去寻找那些 “基业长青” 的秘密,去回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穿越周期的基因:为什么有的公司经历过南北战争、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互联网泡沫,依然屹立不倒?它们是如何在技术更迭的巨浪中完成 “大象转身” 的?
护城河的本质:是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是甚至能对抗通胀的品牌心智?还是某种极高的转换成本?我们要剥开财报的数字,看到底层的竞争优势。
生意的第一性原理:不管是卖药、卖糖水,还是卖软件,好生意的底层逻辑往往是通用的。我们要从这些百岁老人身上,提炼出那些 “不变” 的真理。
有人把标普 500 称为 “蓝星贝塔”(Blue Star Beta),意为地球上经济增长的平均收益。但在我看来,这 500 家公司里,藏着人类组织协作的智慧。
这是一场漫长的长跑。如果你也相信 “慢慢变富” 的力量,如果你也对 “好生意” 有着近乎偏执的好奇心。请关注我,我们从最古老的公司开始,这趟旅程,现在出发。
目前已完成:
【1】高露洁 Colgate-Palmolive 1806 年:我那没出息的狗,吃得比我还贵,华尔街却笑疯了
【2】邦吉 Bunge Global 1818 年:控制全球饭碗的 “隐形巨人”:为什么我们离不开全球化?
【3】麦克森 McKesson 1833 年:全美排名第九的巨头,为什么你听都没听过?拆解美国医疗的 “运血大动脉”
【4】迪尔 Deere & Company 1837 年:比特斯拉更早实现轮上机器人,是一家 188 年的拖拉机厂?
【5】宝洁 P&G 1837 年:全球商业领袖的黄埔军校,是 Costco 开市客最大的受害
【6】史丹利百得 SWK 1843 年:中国的锂电池,正在改变美国水管工的生产力
【7】丘奇德怀特 CHD 1847 年:美国人最偏爱哪家避 yun 套?不是你想的
$Pfizer(PFE.US) $Merck(MRK.US) $Yunnan Baiyao(000538.SZ)
The copyright of this article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organization.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in are solely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do not reflect the stance of the platform. The content is intended for investment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an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investment advice.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conten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