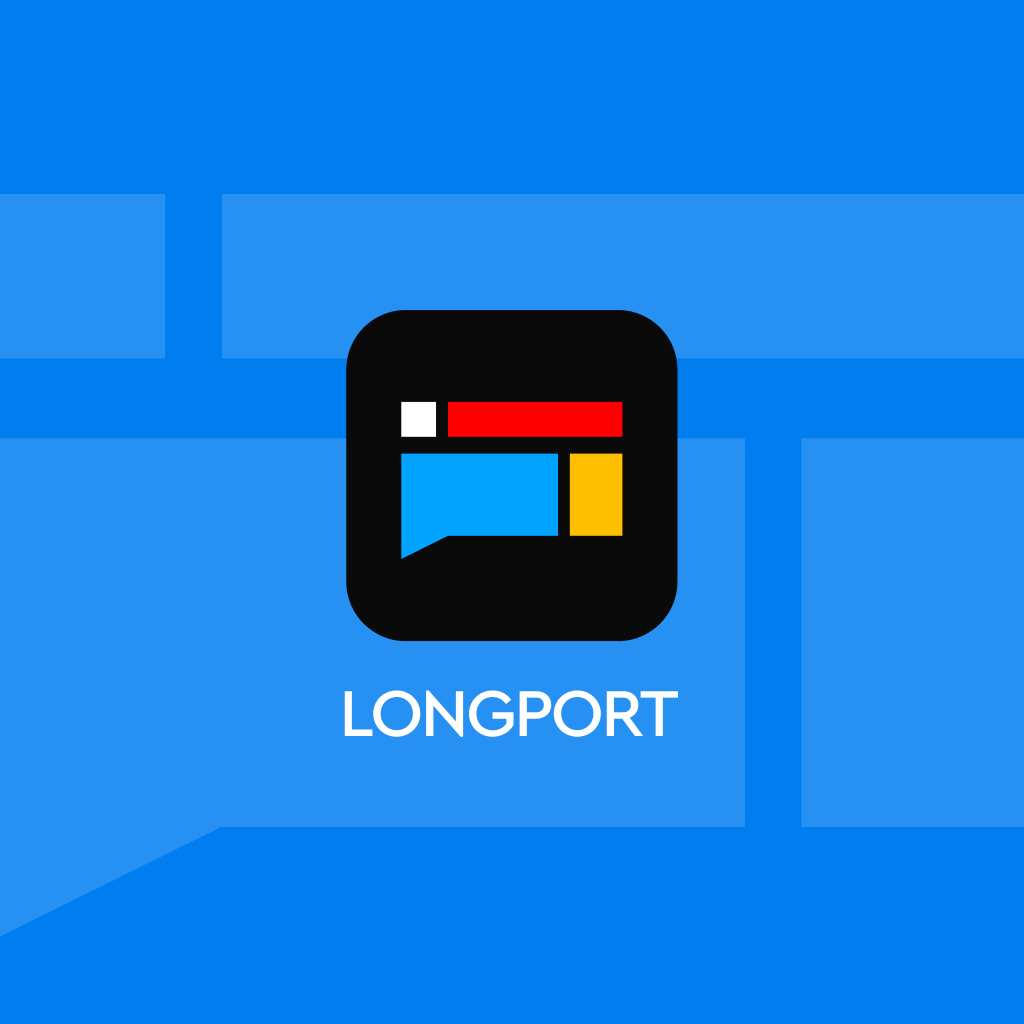
投资里最难的部分,是熬过回撤

红与绿导读:
真正有价值的,是换一套信息系统去理解世界。去和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家、最顶尖的学者、最优秀的企业家交流。
来源:聪明投资者
一
1983 年加入 Baillie Gifford,1987 年即成为合伙人,后来长期执掌苏格兰抵押信托,将其从一只地方性基金带成了全球最知名的成长型投资旗舰。
20 年间为股东带来了约 1500% 的回报,而同期富时全球基准指数为 277%。
他的投资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在特斯拉市值只有几十亿美元时,他已是最早期的机构股东之一;亚马逊是 2004 年左右买入,腾讯是 2005 年买入(刚上市不久)……然后长期持有。
安德森靠着长期主义和想象力,押中了这些超级赢家,构建起 “二八法则” 驱动的长期复利曲线。
2022 年从 Baillie Gifford 退休后,安德森并没有远离投资舞台,而是转向新的平台。
他先成为挪威基金 Skagen Vekst 控股公司 Savik Capital 的非执行主席,如今则担任意大利阿涅利家族旗下 Lingotto 投资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兼创新投资首席信息官。
在新的身份下,他依旧延续 “寻找少数伟大公司” 的理念。
2024 年初,詹姆斯·安德森参加 Skagen Vekst 新年策略会,以 “失效的 Alpha” 为题,直面一个刺耳的现实:市场回报几乎完全来自极少数公司。
从 1926 年以来,美国有 57% 的公司一生回报不及国债;从 1990 年算起,美国股市三分之一的超额收益,只来自 10 家公司;全球范围内,自 1990 年以来,只有 1% 的企业创造了全部超额价值。
市场从来不是均值化的世界,而是被幂律法则,即少数赢家驱动的世界。
在安德森看来,投资的真正难点,不是发现这些伟大的公司,而是熬过它们必然经历的巨大回撤。
美国那 72 家长期最伟大的公司,无一例外都曾多次下跌超过 40%。很多人熬不过去,最终失去了真正的复利机会。
他的观点一如既往尖锐:波动率不是风险,甚至可能是风险的反面;短期主义正在侵蚀整个行业;当大多数基金经理都在追逐季度业绩时,真正该做的,是换一场别人没有在玩的游戏——去寻找那些仍然 “疯狂”、敢于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公司。
怎么说呢,这场演讲非常不同,极具个人特点,甚至有点让人为星辰大海的仰望而血脉贲张。
感受下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比如,“我绝对同意,人必须做一些勇敢、激进的事情,甚至是可能对于自己的能力过于乐观的事情。” 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认定马斯克。
但詹姆斯·安德森心态非常开放。
你看他喜欢的投资人就能感受出来,比如比尔·米勒;他也非常喜欢圣塔菲研究所,对的,就是那所索罗斯、米勒们在此接受 “思维实验” 的科学殿堂……
这就是安德森的投资哲学:想象力、长期主义和指数级力量的信仰。他并不承诺明年的回报,但坚信只要能找到、并守住那少数真正伟大的公司,最终结果会远超市场的平均预期。
二、业绩几乎总是由少数几只股票驱动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失效的 Alpha。以及,我们还能为客户做些什么,帮他们在未来几年中赚到钱。
我其实不太习惯单独谈某一年的投资机会,但我会尽力谈谈背后的底层逻辑。
过去几十年里,我最欣赏的一位思想者,不是金融领域的,而是跨界领域的实践者,是那位伟大的、可惜已经过世的瑞典人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已故的瑞典公共卫生专家、统计学家和世界著名演讲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数据讲解和打破刻板印象的观点而闻名)。
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你应该让数据改变你的认知方式。”
我很高兴今天早些时候有人引用了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英国著名作家、医生,以创作福尔摩斯探案系列而闻名世界)的名言,那我也补一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话:“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进行推论,是最严重的错误。”
那么,我们来看看数据本身。到底什么样的投资行为,才是真正在创造 Alpha(超额回报),真正带来价值?
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些表现完全可以从一个标准化的正态分布钟形曲线里读出来。高斯分布让人们可以进行各种数学推演,比如计算所谓的 “风险”,甚至直接用 “波动率” 来定义风险。
但问题是——这真的合理吗? Alpha、夏普比率这样的概念,真能解释投资世界吗?
这些理论和模型,真的存在吗?恐怕答案是:并没有。
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像柯南·道尔所说的那样保持开放思维。他曾写道:“人的大脑就像空的橱柜,直到你开始积累经验。”
我第一次对这一切产生不安,是因为现实摆在面前:业绩几乎总是由少数几只股票驱动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同行是否喜欢,事实就是:大多数年份,表现全靠三到五只股票。其他股票不重要,哪怕是亏损也无关紧要。真正决定成败的,是那极少数的超级赢家。
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我找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亨里克·贝森宾德(Henrik Bessembinder)。
我还记得,那是在苏格兰最寒冷的冬天,我专程去拜访他。他的研究将美国市场回溯到 1926 年,这是一个极佳的起点。当然你也可以从 1990 年开始,因为全球市场的数据在此之前并不完整。
他做的事很简单:回过头去,用最直接的数据,看看市场的回报究竟来自哪里。
这种方式,正是柯南·道尔和汉斯·罗斯林都会欣赏的。
结果令人震惊,甚至越来越极端,以至于任何试图用 “均值” 或 “正态分布” 来理解市场的努力,基本都是错的。
以下是一些硬核事实:
从 1990 年算起,美国股市三分之一的超额回报(相对国债),其实只来自 10 家公司。
从 1926 年到 2016 年,仅 90 家公司贡献了市场一半的价值增长;如今,这个数字已下降到 72 家。
放眼全球,自 1990 年以来,只有 1% 的公司创造了全部的超额收益。
我可以继续举例,但核心结论很清楚: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均值化的世界,而是被 “幂律法则” 主导的世界。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
我认为,更令人不安的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背后那一整套逻辑,其实并没有事实依据。
要知道,自 1927 年以来,美国有 57% 的公司,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回报低于国债。
换句话说,持有股票本身,并不存在系统性回报。
三、投资里最难的部分
不是发现赢家,而是熬过它们的回撤
既然如此,“均值回归” 又从何谈起?
在这样的世界里,连一个有意义的 “均值” 都很难定义,因为变量实在太大。
而这,将引出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你只有在拉长时间维度、以长期主义视角看问题时,才能看到这些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错误不断发生的原因。
如果你用 “日度”“月度”,甚至 “季度” 或 “年度” 去分析数据,是无法发现这些规律的。
真正的财富创造,必须放到几十年,甚至一家公司整个生命周期的尺度上,才会显现。
短期主义,其实已经渗透进我们所谈论的一切之中。这才是核心问题。
你知道吗?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说——虽然这可能对主办方不太礼貌——我拒绝只谈今年的投资。
所以,当有人问:2024 年会发生什么?
我的答案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东西,只有在长周期里才会显现。
正如我之前强调的,“波动率” 根本不是有效的风险指标,事实上,它很可能正好是风险的反面。
看看美国那 72 家真正伟大的公司:每一家都经历过至少一次、甚至多次股价 40% 以上的回撤。
这些时刻,其实就是市场给你的机会,让你弥补最初没买入它们的错误。
在我看来,投资里最难的部分,不是发现这些公司,而是熬过它们的回撤。
四、投资就是要与众不同
找到那些真正伟大公司的共性特征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模式会延续吗?还是说我们会迎来一个 “百花齐放” 的时代,很多股票都能跑赢市场?
我并不这么认为。
部分原因是,知识产权驱动的公司天然处在一个 “赢家通吃” 的格局,比其他商业模式更容易形成头部效应。
自 1986 年微软上市以来,知识产权型公司就越来越重要,它们的主导性也在不断增强。
但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这个行业本身。
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低效,而不是更有效;短期主义愈演愈烈;最严重的是,投资思维的多样性正在消失。
我尊敬任何愿意去做不同事情的人。但我真正讨厌的,是那种盯着季报炒股、每年想着多跑市场 1% 的做法,根本就毫无意义。
如果你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那样用数据把量化做到极致,或者是做深度价值,那我都是佩服的。
我不希望所有人都按我的方式思考,但我希望他们敢于不同。
所以我会说,我们必须去玩一场不同的游戏,而不是和所有人玩同一场。
我是苏格兰人,我很清楚,我们国家的足球队赢不了世界杯。或许能赢挪威?那倒不难。
但如果换个游戏呢?比如飞镖或斯诺克,哪怕你身材走样,照样能成为世界冠军。
关键在于:你得换一场别人没在玩的比赛。
投资也是一样。
我们该做的,不是 “击败市场”,不是 “预测未来 12 个月”,而是:找到那些真正伟大公司的共性特征。
只要你在某个时点认出其中一两家,并愿意十年持有,其余部分你做得差一些,也无妨。
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 “以不合理的价格买入增长”。
所有人都喜欢合理价格买增长,因为听起来很舒服,很安心。但我要说:在股市里,你不该让自己觉得舒服。投资中,你应该始终感到一种赤裸裸的暴露感。
这,就是以不合理的价格买增长的本质。
为什么不合理?因为大多数公司最终并不会兑现你期望的那种爆发式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确实是买贵了。
但只要其中有那么几家公司成为真正的超级赢家,它们的表现会压倒一切。最终,你还是能走到终点。
我最想传达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我们有幸持有的伟大公司,它们最终的盈利、现金流、营收乃至股价表现,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最狂热的预期。
这件事,往往让投资人产生极其复杂的心理反应。
因为它彻底颠覆了你作为分析师的训练方式。我们从小被教导要理性、要做估值、要去预测,但如果你真的想抓住这样的机会,你需要的却是想象力。
你必须承认:事情很可能不会按你的预期发生,你要能承受这种不确定性。
就拿腾讯来说吧。当年我们刚写它的投资报告时,回头看简直觉得那份分析是短视的。我们根本没法想象,它最终会成长为今天这样的公司。
而类似的例子,我可以列出很多。所以,你必须拥有一种深度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深度的想象力。
可问题是,为什么这变得越来越难了?
我曾和我最敬佩的投资人之一比尔·米勒(Bill Miller),一起参加过一场与查理·埃利斯(Charlie Ellis)的讨论。很多人知道他,他是 CFA 早期的思想奠基者之一,写过大量关于市场有效性的文章。
埃利斯的观点是:市场越来越难战胜,因为整个投资行业已经高度专业化。
我部分同意他的看法。确实,如今行业里有更多人做分析,他们很努力,也聪明得多(虽然未必比比尔聪明)。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正是因为行业越来越专业化,反而让问题更严重。
我来自医生世家。如果大多数医生告诉你一件事是真的,那大概率是真的。但如果大多数投资人告诉你一件事是真的,你最好晚一点再相信。
所谓 “市场越来越有效” 的说法,我觉得根本是错的,甚至是方向性的错误。
为什么?因为数据不会骗人。
今天,全世界大约有 22 万人拿到 CFA 资格。无论他们嘴上怎么说,CFA 教授的核心,依然是夏普比率、马科维茨、有效市场这些投资教条。
可是,你去看贝森宾德的那篇论文,至今也只有 4.5 万人读过。虽然比两三年前已经多了,但差距依旧巨大。
这也直接体现在大多数投资人的行为方式里。而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它已经变得危险。
我担任几所大学的投资委员会受托人。每次会议一开始,大家都在说:“我们只关注长期,季度波动对我们没意义。”
但会议一旦展开,他们讨论的问题,和所有人一样短视。
说真的,我已经厌倦了天天去谈 “美联储下一步政策会怎样”。那根本不是有用的讨论。
这也把我引到今天这个阶段想讲的最后一个点,然后我会分享一些关于未来该怎么做的想法。
五、投资应该聚焦帮助
那些真正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公司
这也引出了我今天最后一个想强调的点: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对基金管理的理解。
我们大多数人长大的时候,都被灌输一个过时的观念:股票市场像 19 世纪一样,是在为社会分配资本,修运河、建铁路、推动人类进步。
但今天,我们做的事,早就不是那回事了。
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化,本质上就是在不断放大我们的自我。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虚荣的篝火》里有一段精彩的描写:那个失败的 “伪英雄” 不得不让妻子来解释自己是怎么挣到那么多钱的。妻子说:“这就像是在烤蛋糕。”
但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真的在烤蛋糕。
他们做的,只是一次次把蛋糕传来传去,每传一次,就有一些 “金色的碎屑” 落在自己手里。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而我们现在该做的,是回到真正烤蛋糕的状态,去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
这并不意味着接受低回报。相反,如果你只是想着赚快钱,往往什么也赚不到。
你需要用一种 “间接式思维”,逼自己去想清楚:伟大的公司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举个最重要的例子,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主题:我们应该聚焦那些真正试图解决重大问题的公司。
我承认,我和埃隆·马斯克之间曾有过分歧,他有时确实让人不舒服。但我真心佩服他当年接受法语日报《Le Soir》采访时说的话。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造电动车,他爆了很多粗口(我不知道翻成法语听起来是什么样),但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你以为我是来找一个轻松赚钱的行业,那你简直蠢爆了!”
汽车产业是极其艰难的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但重点在于: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而电动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
投资人应该始终聚焦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能否通过投资,帮助那些真正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公司?
而要做到这一点,你不仅需要长期主义和想象力,还必须真正理解 “指数级力量”。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认知任务。
六、换一套信息系统去理解世界
坚持长期主义
今天上午,Chip Miller 提到,他认为半导体是上述语境下的独特存在。
我完全同意。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
ASML 曾试图追溯摩尔定律的起点,不仅回到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上世纪 60 年代发表的那篇论文,而是更往前。
他们认为,摩尔定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00 年。从那时至今,半导体性能提升了多少?
答案是:9 × 10¹⁸倍!你不可能不被这个数字震撼!
如果你能预见到这样的演进,你几乎不可能从中赚不到钱;但如果你站在 1900 年,又不可能想象它最终带来的深远影响。
这,才是真正需要的认知。
那么,要获取这种认知,需要依靠什么信息源?
这一点可能会冒犯在场的一些人,但我必须直说: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和券商聊过股票了(除了安排会议)。因为卖方的本质,是把你拉回那种 “猜一猜、赌一赌” 的短期游戏里,对投资毫无帮助。
真正有价值的,是换一套信息系统去理解世界。
去和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家、最顶尖的学者、最优秀的企业家交流。
我们过去最好的投资洞察,或者说,我个人最深刻的认知突破,大多都来自这些交流。从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 SFI),到很多卓越的个人学者,这才是真正的源头。
比如在可再生能源与电池技术领域,我 15 年前就听 MIT 的杰西卡·陈(Jessica Tran)谈到前沿趋势。她当时预测了这些技术未来的可能性,并不是哗众取宠的跳跃式预测,而是一个你可以信赖的发展方向。
这和依赖市场预测,完全不是一回事。
让我最后以一个真正积极的观点收尾,尽管这个世界依旧充满荒谬与灾难,让我重温汉斯·罗斯林的另一句经典之言:“人类的进步,常常是悄无声息地发生的。”
半导体行业发生的指数级变革,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半导体本身,而是向更多关键领域外溢。
简单说一句: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技术手段,我们几乎已经拥有。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合理部署、如何定价。
更令人兴奋的是医疗健康行业。长期以来,它几乎是摩尔定律的反面,有人甚至称之为 “Rom’s Law”(性能停滞、成本上涨)。
但如今,如果你把基因组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人类对生物学的理解可能被彻底改写。
这意味着一场潜在的产业革命。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领域的很多公司,如今并不受追捧,和所谓 “七巨头” 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你问我,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宁愿自己年轻 40 岁,而不是拥有 40 年从业经验。
因为,如果你能用独立的思维、长期的视角,加上这些深层力量的顺风,你所能参与的机会将是极其令人兴奋的。
这会在 2024 年就立刻转化为投资回报吗?我不能保证。
但我也不觉得,这有多重要。
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帮助那些推动世界进步的公司变得伟大。从长期来看,它们会带来远超市场预期的回报。但这种事,不可能每年都发生。
坚持长期主义,这就是我今天的结尾。
本文版权归属原作者/机构所有。
当前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立场无关。内容仅供投资者参考,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如对本平台提供的内容服务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联系我们。

